重讀文學史,繼續讀神話。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山海經北山經》)
其鳴自詨:“詨”音囂,與“呼”、“叫”同義。“精衛”是這種鳥的叫聲,所以說它的鳴叫就是自己叫自己。它本來是炎帝的女兒,名字叫女娃,在東海遊玩時候溺亡,因而化作精衛鳥,常銜著西山的木石,去填塞東海。
讀書時候,沒有老師講到這裡,總要說表現了精衛的情勞勇敢、不具艱險。現在重讀,覺得這是一個關於慾望的故事:溺亡在慾望之海裡,從此所有沈重不堪的努力,都是為了填滿慾望,但所有行為都是徒勞。
人一生命運的走向,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
若是偶然。
人的肉身之舟,承載著靈魂,在命運大河的沖刷下駛向無何他鄉。人既不能迎接幸福,也不能迎接苦難,一切甜蜜和憂傷都是被動地迎頭撞上。這條命運大河裡,每一粒水滴都是偶然。
個體在洪流中,只能被動的接受。
若是必然。
人生每個抉擇,都是往昔之井的映射。你的每一個應激反應,都是因為先天的基因和後天的環境。先天的基因,由遠祖寫入。後天的環境,由無數和你一樣由遠祖寫入基因的人組成。千萬年前山洞裡,猿人被火燒傷了手,千萬年後你選擇這會兒坐在這裡讀我這篇文章。
無數遠古的神話如同一粒粒水滴,你只是這水滴中的一粒,被擠在億萬水滴的大河裡,別說決定河流的走向,連自己往左往右都不能決定。
個體從來不擁有選擇權。
人生所有的所謂“選擇”,只是精衛對銜哪一塊石頭的選擇。
我們銜著房子丟入慾望之海,接著銜著車子丟入慾望之海,名譽、金錢、愛情??一一丟進大海,永無止境。
佛家拋棄了慾望,就是精衛拋棄了大海。填不滿,於是視而不見。
昆德拉在小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的開篇,這樣寫道:
永恆輪迴是一種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讓不少哲學家陷入窘境:想想吧,有朝一日,一切都將以我們經歷過的方式再現,而且這種反復還將無限重複下去!這一譫妄之說到底意味著什麼?
永恆輪迴之說從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遠消逝,便不再回復,似影子一般,了無份量,未滅先亡,即使它是殘酷,美麗,或是絢爛的,這份殘酷、美麗和絢爛也都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對它不必太在意,它就像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一次戰爭,儘管這期間有三十萬黑人在難以描繪的淒慘中死去,也絲毫改變不了世界的面目。
既然生命只是永恆輪迴,每一分失去或者得到都將再現,那何必在意得失?如果永無回復之可能,那麼所有的經歷都只能在過去的時空,了無份量,何必在意?
精衛不斷填海,先挑這塊大一點漂亮一點石頭,還是先挑這塊小一點抽一點的石頭,根本毫無意義。
我們遠古的祖先不斷重複精衛填海,又從往昔之井裡拽住我們,不斷重複精衛填海。人類世世代代永恆輪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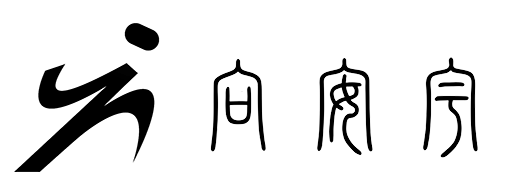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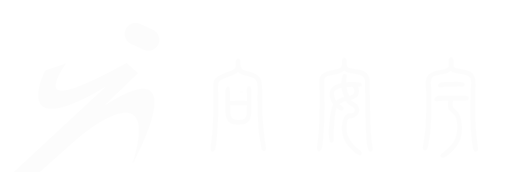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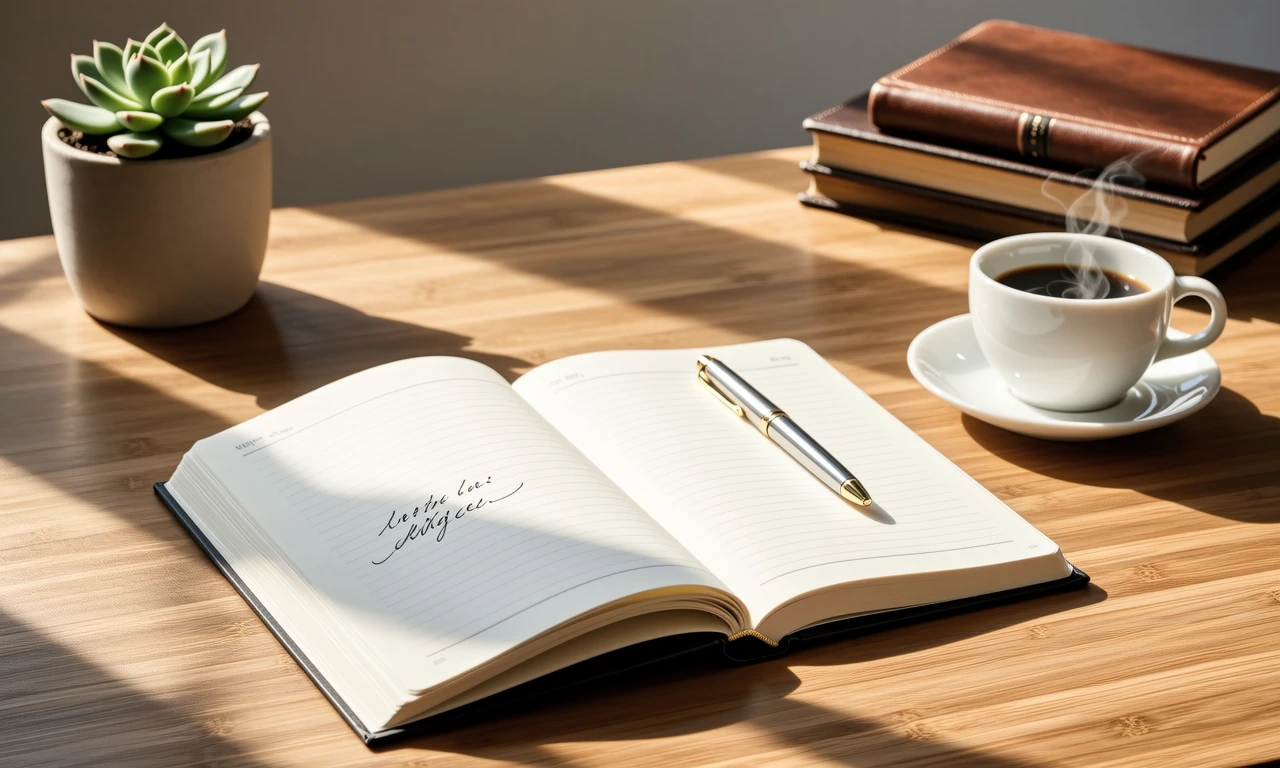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