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時間:2020年7月15日(三) 14:30-17:30
-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
- 講者:廖慶松
- 講題:剪輯/青鸞舞鏡,隱身於明鏡之後
- 文字記錄:鍾佩樺

我是在民國62年底參加了技訓班,民國63年就進了中影的剪接室。我的老師剪過《龍門客棧》、《周處除三害》,都是台灣最好的剪接師,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基本功就是:這個太快了,這個太慢了,這個空鏡只要兩秒。從來不談主題、不談內容、不談感覺,完全不談。各位知道剪接是電影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個人不是強調剪接至上,我認為剪接是一個平台,是所有人站在上面的平台,如果沒有好的畫面,音樂不存在;攝影如果沒有剪接,成功也不存在。所有人基本上都站在剪接身上,包括導演。編劇、導演、美術,最後都透過最完整的形式表達,這稱之為剪接。所以剪接負擔的責任非常大,雖然我還是不認為要特別去強調剪接的形式或什麼,剪接就像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所有人在上面表達的方式。
但是剪接很可能是不被看到的,為什麼呢?因為攝影師有一台攝影機,而且攝影機架出來,你就會很尊敬他,鏡頭那麼長,架式十足,每個攝影師都有點高大,後面又跟三個助理,事實上我還挺羨慕的。一進去錄音室就一個大銀幕,有一個console操作台,有的打開還可以分裂式,一個大銀幕在那邊刷刷刷,看了就立正了,這設備太棒了。美術指導來畫了一些圖,哇,聊服裝什麼的,包了一堆東西參考,這太專業了我做不到;音樂家手往keyboard一放,問什麼key,每個人都有裝備。那我們剪接來了,就只是拿著一個notebook打開,把硬碟插上去,這件事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以看起來就沒有那種可以翹起鳳凰尾巴的裝備。攝影師說我們現在上大砲,就二十個人,架式多足;我們叫助理過來要剪接,結果是把notebook打開這樣,很不稱頭。
一開始導演有個想法,有了錢開始編劇編兩三年,組了團隊,劇本原來就有它的缺陷,但趕著要拍也不管,就一直走、一直做,每個人都一直交棒。現場一直拍,大家都可以往後推嘛,攝影拍完後面有一堆人做,反正後期也還會有人做完,交棒到你這邊時,你也想往後面交,發現我的後面沒人了,這是我突然發現剪接很重要的原因。我後來才發現我這麼重要,但我好痛苦,為什麼?所有沒辦法解決的事情,基本上一定要在剪接完成。導演沒想清楚的、編劇沒想清楚的、現場沒拍好的、沒錢拍的……,到剪接時,老闆就叫我要剪好。我心裡想說「你是在說什麼?」然後預算很不幸地到剪接前都用完了。我想各位一定很多這種經驗,製片跟你聊說我們錢都沒了,本來三十萬的酬勞,現在只能五萬。拜託啦,不然我找更便宜的剪,你突然發現身價瞬間降低。但當你面對影片,責任感就上身了,你會發現捨我其誰。如果我不剪好,後面真的沒人,假如你真的喜歡剪接,你會發現這個困難其實就是對你的大挑戰。
如果你不愛剪接,就不要做剪接這行
繞回來講,我進了中影大概三個月就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叫侯孝賢,我們倆就開始工作。他幫陸軍總部拍了一個叫《陸軍小型康樂》,是用16mm底片拍的,我記得在桃園龍潭陸軍總部拍的。我有幸又參與了台灣電影新浪潮,新浪潮的成立是在中影,這是有背景的因素,因為中影是國民黨之下的一個機構,而且是用國家預算的。當六、七○年代台灣正在轉型,從戒嚴時期慢慢開放,但還在戒嚴的尾巴,我們還發生「削蘋果事件」,我是《蘋果的滋味》的剪接。我有幸在那個時代,從台灣的經濟、社會轉型到政治轉型的過程,接連大概十年被幾個導演輪番轟炸,那年代真的很痛苦,基本上365天有兩百多天都在熬夜。現在四十年後回頭看,我很開心有那段時間,因為那段時間對我個人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變就是大量的轟炸,我一年用手工要剪六到八部片,每天就坐在剪接機上,所以我三十歲就研究營養學、維他命,因為我怕有一天剪片子剪一剪,好累趴下去睡就永遠不起,我就完蛋了。
我進去就當《英烈千秋》的剪接助理,就看我師父用手拉著剪,那時候沒有機器的,我站在師父旁邊看,旁邊是丁善璽,他前面都放個盤子,上面有各種水果,我在旁邊都一直看水果。但我對自己要求,只要師父停下來,我就知道他要幹什麼,當助理你該要求自己要當最好的助理,腦筋跟師父同步,我現在碰到各種助理就很難有這種現象,可能時代不一樣。也許我們那個年代都非常手工業,師父都採取身教,因為他也不會說什麼言教,沒有談過這個節奏、命題、形式、風格、內在的什麼東西,所以我只能看著他做,他一停下來我幾乎就知道他要幹麽。我師父超愛我,所有他要做的事情我都超前布署,比現在疫情還快。他有一天突然開門跟我說:小廖,有七件事要做。我就回答:師父,我都做完了!他說:喔,很快。我自己想到就一直做,為什麼?我很愛剪接。
各位要當剪接,第一個很重要就是你們要很愛剪接,如果你不愛剪接,就不要做剪接這行,因為這一行又重複、又煩、又被壓迫、又被押著要改,最重要的是錢常常拿不到,這一點我是最在意,但我都講不出來。我到現在還是都說你有就給我,結果是有給我,但都比我想像中低,但我沒辦法,因為我太愛做這件事了。後來新浪潮導演一個接一個來,幾乎不停的,你願意為它一禮拜只穿一件衣服,因為都沒有回去,一直待在那邊。但是他們前門出去,我就走後門出去,為什麼?這票留美的導演很討厭,都講一些我搞不懂的事情,我被他們刺激了,所以只要他們一出去,我就從後門出去買書來看。因為你要懂得吸收新知,不要覺得卑微,覺得他們留學怎麼樣。現在留學已經很平常了,學習管道也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願意接受新的東西。
你一定要好奇,因為你不好奇,無法面對所有影片的資料。我盡量保持我的好奇心,保持對新知的求知慾,要去瞭解背後的事件,我跟侯導聊天都是聊事件、聊人、聊社會新聞,往上推到緣由,往下推到未來的發展。我們兩個像是現在的名嘴,坐在那邊討論,因為那時候政治情況一直在改變,我的筆記像政論家寫一堆事情,隔那麼多年我現在看,才發現我們都對時代感覺很敏感,例如哪個總統第一任上去,我的筆記竟然寫首先他要把什麼黨本土化,如果不本土化,後來會遭遇什麼事……,後來都實現了,我們兩個都在聊這些事,但是也是在練習,你的好奇讓你對很多事情有一種穿透力,知道越多,對一個剪接來說是最好的,很多事情要系統論地去看待,系統性地把你的理論擴展,因為影片離不開主題及風格,事實上是很完整的系統的概念。
我記得在剪《悲情城市》時,有一段梁朝偉跟辛樹芬聽古典音樂〈詩人與農婦〉,然後兩個人在聊天。我很努力把它剪好了,有一天杜篤之跑來我門口敲門,他跟我說:「欸,唱錯了,音樂沒這麼長,你剪太長,要不要把畫面修一下?」他的意思是我音樂用太長了,事實上音樂沒這麼長。那時侯導坐我旁邊,我就回頭說:「導演,我剪好的片子,你認為他應該將就我,還是我應該將就他?」後來杜師傅就把音樂延長了。因為畫面那麼完整,又看不出破綻,為什麼需要因為音樂剪畫面?我當然不是剪接至上主義,電影工作是系統性的合作主義,該誰站出去就由誰站出去,誰應該solo就誰solo,不是說我永遠要當solo那個。但還是要從影片的整體性、系統性,經由導演的概念傳達得最好,或把演員呈現得最好的,這才是最重要的。沒有應該哪個人一定要特出的,但該你特出時,你不能退卻。像是剪接,你是負責最後工作的人,這個責任是不能放棄的,這很可能是整個影片最後一關。
以觀眾為感受主體的情感邏輯
《悲情城市》劇本這麼厚,一共有兩百多場,結果最後侯導拍幾場?拍一半而已。前兩週我還傻傻地按場次表的號碼剪,但影片看起來很奇怪,看得懂又看不懂,好像又懂,最後完全不懂。因為他1、2、3場拍,4、5場不拍;6、7場拍,8、9、10、11場又不拍了。我跑去問侯導說:「你這樣拍我剪不下去,幹麼不拍那些場次。」侯導也回得很酷:「我覺得很囉唆,所以不想拍。」但你覺得囉唆,我就變困惑啦,看下去我就看不懂,這就造成你的剪接生命快結束了,剪不下去了,應該要放棄,但是危機就是轉機對不對?我想了好幾天,我回去就跟他說:「我們可以做一件事嗎?」我當然要先試探一下,因為天底下有個最自我的動物,名字就叫導演。你要去談事情,還稍微要照顧他敏感的自尊心,我想大家都深有同感,我吃了很多這種苦。他問:「什麼事?」我說:「可以讓人家看不懂嗎?」他就說:「好像沒辦法,但我不能讓人家不尊敬我們。」我說:「那現在我就用一種詩化的方式去剪。」
事實上我那時都在看唐詩,我最愛的師父是杜甫跟李白,但杜甫對我比較好,因為他把事情講得更清楚。杜甫是個非常用功、深情的人,但他的詩是有理論的,他的遣詞造句在修辭學跟情感上是非常貼的。《悲情城市》是fix長拍(固定長鏡頭),每個影像都像杜甫的七言律詩,一個畫面都像一句詩句,一個畫面就是完整一個情境,我就用詩句的概念剪。我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因為他拍得不完整,所以我只好把觀眾請來當主要訴求的對象,所以我讓觀眾變成主觀看這部片。因為詩是很主觀的敘述體,簡化、凝煉,但有個很重要的是「感受體」是誰?是觀眾,所以觀眾的情感是剪接時要計算的。因為侯導少掉了「故事邏輯」,但我可以用「把觀眾當感受主體的情感邏輯」去描述這電影。當觀眾成為主觀的感受者,所有的省略跟時間的跳躍就變得很正常,我就只要控制劇中人的情感邏輯,跟觀眾欣賞主觀的情感邏輯,當你不說故事給他聽,他自己就變成主觀的感受者。
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就傾向讓觀眾成為主觀感受者的存在,他的形式跟侯導不一樣,他是用很長的鏡頭跟演員的移位,製造一個不被削過、不被剪接處理過的時空,給觀眾一個完整而自然、從頭到尾的情緒,觀眾非常非常投入。雖然他的話一直重複,但這是他電影的情緒,他把角色情緒一直揉,揉到你必須感受得非常清晰。侯導是另一概念,是極自然、極簡主義。我有段時間跟侯導討論安哲羅普洛斯,那時還以為他們很像,我就問侯導他們是不是很像,都是長鏡頭、場面調度,他只回答我一句話「我覺得我自己跟他不像」。有次我上課把《永遠的一天》整個討論過,突然發現他們完全不一樣,面對觀眾的狀態是一樣,但形式完全不一樣。所以對觀眾來講,站的位置是一樣的,但表達的情感還是不一樣,這就是藝術的可貴。我跟侯導曾經在金馬學院上課,上完課後,學生跑來問我,廖桑你跟侯導講的都不一樣,你們講的是完全相反,我的回答是:相反都一樣啊,圓形的圈,我們背對背,但我們兩個就在隔壁,不要想成一條線,把線一拉,我們在線的兩端,其實我們在隔壁,這就是藝術家的思考。你們一定要彈性地去面對影像,因為影像像一個人一樣,影像擁有一個人所有個性。
《悲情城市》原劇本其實是非常邏輯的程序,事件是有很清楚的時空過程,但我如果照那樣剪,觀眾就變成又在聽故事,我不要讓他聽故事,我要讓他面對角色情感的本身,我要用情感邏輯,我要讓他看了像是詩一樣的感覺,所以這故事就被我倒裝了。最明顯的是,本來劇本上梁朝偉跟辛樹芬分開後,就走梁朝偉那條線,梁朝偉在228事件當天的火車上被人詢問。但是我走了辛樹芬那條線,當梁朝偉走了,辛樹芬寫信說大家要照顧他,突然發現樓下有聲音,結果走下去,醫院來了很多暴民,228事件爆發。我是用情境來讓觀眾進入的。過幾天之後,梁朝偉回來找她,他們聊一聊,梁朝偉突然昏過去了,她就問他,梁朝偉才開始寫字,寫說228當天遭遇了什麼,才接火車的戲,所有事件都是透過角色的情感來跟觀眾接觸,整個片子就變成處處在跟觀眾情感對話,看下來當然可能故事沒有很懂,但是會非常有感覺。

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剪輯邏輯
再來我會談《風櫃來的人》,這部片很特別,當時我跟侯導合作了十幾年,突然發現剪片剪到很無聊,都是基本動作。因為侯導早期的片子是非常商業,跟觀眾很接近,他可能被新浪潮導演帶壞了,原來一個很土的侯導,突然變成場面調度、談話都不一樣了,談得我肅然起敬,我都覺得他講的話跟以前不一樣了。他把好漢鞋的後腳跟都踩扁,拿一個很土的包包,每天都穿一樣的衣服,好像是鄉下來的人。後來拍了《童年往事》才知道他是廟口派混過來的,我覺得很好玩。剪《風櫃來的人》因為我們工作十年了,面臨轉換關卡,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說故事,影像邏輯剪到很累。我記得剪過一部片《立體奇兵》,大概剪了兩千個鏡頭,每天都在連動作,我竟然吃飽飯一邊睡覺一邊剪,昏昏迷迷就剪了一大段,因為那是標準動作,尤其在早期的國產電影,分鏡都分得很仔細,有導演還是那種分鏡好,你只要把停格、拍板剪掉,連一起都通,還很順。為了省底片,演員常常遠景拍一個,停格,攝影機往前推,然後繼續拍,很多時候演員就站著,然後換鏡位,攝影機架好繼續拍,剪接一接還可以連,很厲害。一個片子九千呎左右,給他一萬多呎,剪完還太長,這個我自嘆不如。因為我當導演,超支,還掏錢買底片。
好萊塢片子說故事說得太好看,因為他是從第一個鏡頭開始,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四到五時你就發現你會follow他的邏輯。當你開始分鏡,很清楚地裡面就有說故事的人,說故事的人通常就是導演,但是說故事有個麻煩就是,觀眾就會跟著說故事的程序一直說過去,這個事件必須要很飽滿,衝突要很精緻,所有東西都要很厲害,編劇方式要非常棒,不然邏輯剪接會不好看,這是商業電影最難的地方。各位剪商業電影時碰到困境,剪半天都不好看,因為在傳達故事最重要的是說故事的浪漫、衝突,所以在剪這種邏輯時,最好是故事精彩、人物立體,這就是商業電影最困難的地方,就是編劇。因為好的商業編劇又好看、又有衝突、又有人物,事實上是超難。
不要以為看一些編劇書,像是〈救貓咪〉,我根據編劇書編過,還在課堂上討論那個劇本,我跟你講,全世界最難看。第一個人物不夠立體,第二個人物沒有感情,第三個為何要說這故事。當你按劇本宣科時,根本就沒有自己的主題,沒有痛苦、情感要傳達,事件跟情感一點關係都沒有,看起來就是零零落落,超難看。就跟我年輕進剪接室,我師父對我很好,我一進中影,在後面站了幾個月,我師父就拿一卷片子來給我剪,你知道我得到這卷片子有多爽,我學習了幾年終於可以表達了,我對剪接的一腔熱血終於可以表現。一場戲剪了三天、四天,拿去公司播映室放,是我這輩子看過最難看的電影,概念太多,每個鏡頭都有每個解釋,我都設計半天。我很用功,很有概念,但很沒有經驗。所以剪接有個很重要的事情,盡快取得經驗,而且要犯錯,越早犯錯越好,要犯錯就在學校把錯誤都犯完,在安全可控的範圍把錯誤犯掉,趕快得到經驗,對後面的工作會更好。
談回《風櫃來的人》,當時我就很悶,剛好電影資料館在放法國電影展,把所有最好的新浪潮電影都放了。看完了我突然發現,人家拍的片怎麼是這樣。法國人最棒的就是拍人物的感情,拍一個人、男人跟女人、兩男一女、兩人三人的情感拍得非常好,而且拍到情感深處,還傳達了所謂他們的文化跟概念。有個片子讓我很驚訝是《斷了氣》,我們後來才知道為什麼畫面常常斷掉,因為他底片很少,他沒辦法從頭來,所以他叫演員不要動,換底片後繼續拍,然後把中間的接頭剪掉。所以你看他演一半都跳一下,那不完全是風格,也是因為沒底片,換底片再接起來的關係,這也成立啊,還有一種美感,看了好爽喔,可以剪得那麼開心。還有一場偷了車去外面殺了一個警察,變成史上經典畫面,那可能是在很短時間內,把一個人放浪的個性,表達得非常清楚。去看法國電影不是說好要去看,只是時間到了剛好去看,但跟你個人的情境剛好配在一起。剪得很煩,一直在重複,這個重複讓我有點沮喪,突然看到片子,讓我有一種刺激,原來很多事情跟我想像一樣,我只是沒有膽去做,但是別人都做了。
我也請侯導去看,我不知道他看了沒,但《風櫃來的人》拍回來,我覺得超棒,因為他也跳開了以前的視角,事實上我們兩個都被刺激了。剛好《風櫃來的人》是表達當兵前的躁動,我就跟著鈕承澤的年輕躁動,我就把自己當成年輕人的感覺。我記得當時在看一本書叫〈水平思考〉,這種思考是當你想像事情,不必垂直鑽一個洞,因為我們思考很容易很垂直,就一直鑽,我們應該各點都鑽很多洞,這是一個思考的專家講的,就是說你對處理事情要有更多想像跟方法。我最記得有一個叫「中間謬存」的方法,你找不到方法時,事實上可以用別的方法去刺激解決。我記得我那時在用digital betacam,片子常常剪不出來,我就快轉digital betacam,然後突然讓他停,停在哪個畫面我就剪哪個畫面。別人看了就問我怎麼這樣剪,我就說沒辦法,我不會剪,我就用一個錯誤的方式來刺激自己,事實上有一半的機會可能是對的。因為你用功,所以任何的錯誤跟正確,都是很清楚的sign,轉好幾個彎才會想到的事情,突然一接,看起來畫面是錯的,但如果身在其中,這可能會提供一種解決的方式,你可以天馬行空去解決。我有時還會定時,走15秒就停,或是就讓它亂走,你要相信你有一個剪接的夥伴叫命運。
事實上有很多朋友可以幫你忙,但也有朋友在幫倒忙,我在剪《戲夢人生》時,常常有侯導的朋友來,他們就會問侯導剪到哪裡,會說要看一下,朋友還是有頭有臉的,就建議侯導應該怎樣。我聽了就想「完了!」因為他那句話,我要花八小時,把片子拿回來重看,當時是用拷貝剪,都用膠帶貼,只有一個拷貝,我要把膠帶撕掉,再用朋友的意見剪。剪完看一下,突然發現什麼都不是,還要再改回去,就這樣一天都不見了。後來侯導有朋友來,我們都是盡情招待、不讓看片,因為實在太尷尬了。時代不一樣了,現在就是非常大方,所有人都可以出意見,反正用電腦,更棒的是請坐下來剪個版本給我看,我完全不介意。數位時代請大家多表現、多表達,不要在意,重要的是你的判斷,你自己準不準。
《風櫃來的人》因為年輕躁動,我的剪接開始跳tone,甚至主觀到連來回intercut(交叉剪接)都沒有。例如有場戲是鈕承澤在看電影,銀幕上在演《洛可兄弟》,我從《洛可兄弟》直接就跳回,通常剪接一定會這樣剪:他在看影片、跳回來他在想、跳過去才會轉回記憶。我沒有,我就讓他坐在那邊看,直接跳影片《洛可兄弟》的畫面,演到一半就黑白跳彩色,跳成他爸爸的回憶,我就沒在管接片子的邏輯,但觀眾還是看得懂。我跟著他的情緒轉換跳躍,片子就很跳tone,在那年代很多人不能接受那樣的影像,但都覺得很過癮,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情感邏輯。
剪接至少有兩個邏輯很清楚:第一個,說故事的邏輯,但這種邏輯有一個缺點是,通常有會說故事的人出現。你說故事,觀眾就被動,看好萊塢電影觀眾都是被動,但好萊塢有很強的編劇,如果真的要拍商業電影,請把劇本寫好,這個真的很難,因為對角色要很有研究,寫商業電影絕對不比藝術電影簡單。好萊塢一個劇本可能十年、二十年還在寫,中間經手了十幾個到二、三十個編劇都有,甚至還有人負責寫對白,這都有可能。他們要的是什麼?衝突、人物立體、情感飽滿。雖然看起來很設計、每次都很精準,但每次你都會被打到,表示老方法有用,但老方法一直在換人物,人物跟事件一直在改變,事件、人物、情感決定了好萊塢電影。當然更重要的它有很多聲光特效,有大明星,看故事看得很過癮,但那劇本是難寫的。
另一個是藝術電影,你要從靈魂面去影響別人,藝術電影比商業有更多可能性會被流傳更久,因為它跟我們的心靈很接近,跟心靈、生活能夠溝通的東西才會留在你的腦袋裡。商業電影看第二次就沒有更多好奇,這是商業電影的宿命,但所有人都要擠進去看第一次,它要求的是更多人對這電影的喜歡,要的是大階層、大範圍的觀眾喜歡,而藝術電影則是要去所有人的心靈面。這兩個真的都超級難做,但你當剪接時,分際要很清楚。

發展剪接師的兩種矛盾能力 系統性與同理心
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都一樣,你真的要瞭解你的人物,剪接師要訓練的是同理心,比如說演員在哭,你會不會想哭?如果你很酷地看著他「哭得不像,看得很不爽,拿掉!」不是這樣。你跟角色要同步,我覺得這很重要,剪接師不只是一個非常理性的批判者,還是情感最深入、可以交融瞭解的那個人。有人可能會說,這聽起來有點難,確實,在剪接師的身上、靈魂上會有一種打麻花結的感覺,你需要去發展兩種能力:第一個是對所有系統都要瞭解,瞭解攝影、編劇、音樂,混音、調光等,能瞭解越多越好。我當過編劇、監製……,所有工作都做過。你真的要發展出兩種矛盾的能力,跟音樂家的左右手彈出不同旋律一樣,一個音樂的表達如此複雜,需要你具有不同的協調能力跟表達方式。當你負責一個片子最後的守門員,你在建造一個完美平台,讓大家站在上面表達時,你需要給所有人找到最完美的影像傳達形式,真的需要所有的理論、經驗。當然現在講的是我個人經驗,你們也許有別的經驗,我只能從個人經驗來談這件事,但我的確把所有部門的事都做完了,我看事情時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處理方式。
另一個就是同理心,非常非常重要,當你看到演員的表達,有人說演員沒演好是導演的責任,我自己感覺,演員沒演好是剪接的責任,我認為導演有責任,但我的責任比他更大,因為最後演員的表達是在我手中完成的。我曾幫人剪過片子,所有人都說這人是這鍋粥的老鼠屎,把片子演壞了。我仔細看了老鼠屎,我覺得他不像老鼠屎啊,我只能告訴他們,你們可能用他用錯地方了,你們把他擺錯地方。我後來把他調到另外一個地方,後來人家就說他怎麼變得這麼會演戲,所以你的同理心要去感受他,感受角色應該在哪裡。
對系統的瞭解跟解析當然很重要,尤其對人物、劇本的瞭解,我當然也很希望各位要瞭解劇本分析,因為我發現很多剪接師都不懂劇本分析,這有點危險。我們學電影當剪接,第一個都被形式著迷,很容易在形式上剪得很開心,但更重要的剪接背後的思考是「你要表達什麼?」你透過對導演、劇本的瞭解、對演員的表達,或是對整個片子的形式、內容、風格,還有潛在裡面的情感,它具有的靈性,包括所有可能的靈性感覺,你去觀察到底應該怎麼表達。影片完全具有一個人的感覺,我認為每部片不管長短,都像一個人,請你面對影片,把它當人對待好不好?而且當成一個平等的朋友,千萬不要磨刀霍霍向豬羊。你以為影片可以隨便剪的嗎?好像你是上帝可以改變它?絕對不是,你對朋友也不會幹這種事,你還是會跟他聊天,先聊清楚這個人想幹麼,透過他的神色瞭解他的過去。先瞭解他,才可以透過對整個系統的瞭解,知道他應該在哪個位子,要有這樣的分析能力。大家對表演、編劇還是要瞭解,至少對劇本結構、人物本身也夠瞭解,對劇本跟人物的瞭解會增加你在影片處理時的清楚狀態,至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影片是藉由人物表達、行為模式來傳達,人物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你對整個影片製作系統的瞭解,有助於最後處理它的問題。
另外一個極端,達到情感面的極致,這部分就靠最深刻的同理心,在一個剪接的身上,突然要有極端理性跟極端感性的確很難,就像演奏家一樣,左右手可以做完全不同的表達,但要當個好的演奏家,確實要把自己練到自然反應。你必須站在理性傳達及感性傳達的極端,不知道能做到什麼程度,但要有這種想法,希望去把它做到。理性到一個誇張的程度,但同時要感性到演員一點點表現都能牽動你纖細的心,都可以知道他表達得好不好、他在想什麼。也許只有透過兩方面的訓練,你才能走在中間。以佛家或美學的觀點,中間叫「中觀」,中觀也接近人平常的直觀,直觀就是一種最本能的反射。這訓練比較難,但需要的本能反射是「充分鍛鍊後的本能反射」,也許歷經見山是山,到一個程度見山不是山,最後見山還是山。
當我學電影學了十到十五年,包括在剪新浪潮,我是不哭不鬧不笑,只寫筆記,就是說我看任何片子,腦袋都在研究,我最多看一部片看了29次,從剪接看到錄音、調光,年輕就花很多時間看片,每次看的都不一樣。這樣花了十到十五年。而且真的酷到不行,都不笑,就盯著看,好像這樣才專業的感覺,我被兩個片子逼到絕境,一個叫《恐怖份子》,一個叫《戀戀風塵》,在三個月內我要剪兩部片,因為侯導比較大方,就早上剪《恐怖份子》, 晚上剪《戀戀風塵》,但很危險。第一天晚上《戀戀風塵》看起來像《恐怖份子》,侯導嚇到,他說銀幕飄得滿恐怖的,我們看了就發呆,覺得是恐怖片。侯導覺得不行,就說等楊德昌剪完他再剪。完蛋了,壓力都在我身上,因為楊德昌會把侯導時間都用完,你不知道我壓力有多大,年輕剪接師又使命必達。我一輩子只做了一次first copy就是final copy,就是《恐怖份子》,大概花了一個多月就剪完。我到現在還不相信我會做這種事,我怎麼會是這種人?我從來沒有這麼不尊重導演,那時完全是一廂情願文青的概念,哎唷,我一定要保護侯導,就開始剪《戀戀風塵》。我記得剪完的那一天,我放一個ICRT的音樂,一個人在跳舞,就是壓力到一個程度,狂跳亂跳,完全不知道我在幹麼,我覺得是一種情感的發洩,擔子終於放下了。
然後文青就是要用功,馬上去看金馬影展,看了薩雅吉雷的《大地之歌》。我一進去銀幕就0.05秒到我眼前,我嚇一跳,我完全不知道這個sign是什麼,但是很奇怪,從那天開始,看電影我又會哭會笑了。最重要的是,我看《前進高棉》好班長跟壞班長在對待村民,我哭得如喪考妣,我完全跟世界又結合了,十幾年後我的身心靈又回來了。我原來看電影身心靈是分開的,腦袋看這個,心沒有在感受,因為我沒有站在感受那一邊,我站在分析那一邊,完全是理性,突然發現我完全可以用同理心看電影,分裂的身心回來了,從此剪片又會哭了,我現在該哭都哭,這個就是我覺得你很認真面對工作,你真的會在裡面找到訓練自己的過程,我只是從我的思考,當然導演只要一走,我一定買書來看,看一堆書。

自我對話與自我鍛鍊 穿透影片最深處的情感與靈魂
再來談對自己的訓練,我談的都是個人經驗,我沒有希望你們跟我一樣,不然你可能會被認為是瘋子。至少在我非常年輕的時候,我總是放一本筆記本,包括我在睡覺做夢,夢中我會拿起筆來寫筆記。第二天就會看到只寫一半,另外一半在地板上看不清楚,我非常著迷於這些事。我記得我二十多歲時就寫了一本電影轉場理論,看了一堆書就自己寫。我很愛看各種東西,我就是一直寫筆記,從十七歲到七十歲都在寫筆記。筆記是跟自己對話的東西,很重要,你不必寫得好像以後要出版一樣,只是給自己一個memo。我希望各位可以跟自己對話,包括客觀的、感性的,也許這對你在理性跟感性兩端的訓練很重要。我四十歲開始打坐,時間長達五、六年,打坐很重要的一點,是取得你情感上最標準的一把尺,這尺叫什麼?叫「空」。空就是完全不去想,因為打坐是要讓所有雜念都走掉,這個狀態很容易讓你變成一種狀態,變聰明,很會說話,記憶力變很好,但這都是過程,最後要回到一種精神狀態,看事情可以非常客觀,但客觀中又有主觀。你身上有一把到哪個時空都標準的尺,不會因為七情六慾而改變那把尺,這把尺對一個藝術工作者非常重要。
再來,我又慢跑了四、五年,我從靜態的靜心,變成動態的靜心,跑到我人在動,地是停的。我在訓練自己內在的心性,當然都在寫筆記的過程。再來我打籃球打了六、七年,不是跟別人比賽,每天自己練,練我跟球的關係,一開始球跟人混不在一起,後來能混一起,我又能讓人跟球是分開的。我講的是你會從生活中去鍛鍊自己。現在走路,完全是快走,一直走,走得一心不亂,當然走路對身體很好,我跟各位講,能走路就走路,一小時要5.5公里,對你心肺肝的功能都很好,我深受其益,因為我年紀到了一個程度,心臟擴大,走了六、八個月,心臟縮回正常的大小,第一次看到健身怎麼可以對身體這麼好。所以各位永遠要訓練自己,無論是肉體或心靈訓練,永遠不嫌慢,你對身體跟心靈的訓練都會回到你個人的系統,最後當然要回到剪接的能力。因為剪接的人精純到什麼程度,影片就會好到什麼程度。各位要相信,更好的自己,剪的片子應該比你現在更精彩一點,因為人變得更好、更精純,你有更大的穿透力,去看到影片最內在深處的情感或靈魂。透過你對它的瞭解,不管是理性的瞭解或感性的認同,或是你對所有操作過程的瞭解,去慢慢處理。因為你的更好,影片就會更好,事實上你是會影響到一個片子變得非常好。
不幸地我們永遠就在當下,只能做我們在當下的狀態,但我們保持精益求精,對自己有要求,永遠不要怕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有幸跟一票新浪潮導演,或是跟侯導合作。侯導是我生活中的一根刺,因為當我很高興,他就會跑來說:「廖桑,你以為這樣就夠了嗎?你肚子這麼大。」他就到處拆我的台,我稍微膨脹一下自己,他就來拆我台,不知道他是什麼心態。但我很開心,因為有個人永遠不會認為這時候我應該開心,甚至我們對所得到的榮譽,那個開心就是一兩天。永遠不要減少對自己的要求。每天的一小步,每天的一點點,經過一年,你知道跟那些不進步的人相比,你站在半山腰,他還在山下。每天的一點點進步,事實上是平方的改變,不是等比級數的改變,而且量變累積質變。對剪接來講,我們可能學到很多的技巧,最後還是要回歸是你的改變造成影片的改變,是你的更精純,造成影片變得更精緻,永遠不要停止對你自己的改變、努力、鍛鍊。
我只是給你一個概論,剪接師的養成要靠你們自己去做,多看、多聽、多讀、多寫。你們要像參加國家隊那樣每天鍛鍊,我參加國家隊就是被新電影操了十年,我現在很感謝那個十年,我發現我真的被鍛鍊。所以各位找很多時間鍛鍊自己,剪片時你當成自己一個里程碑,很認真去面對,所有認真跟努力都會在累積過程被看到。最重要的是你對你自己、對工作的觀點,還有你自己希望未來做什麼,這才是影響你成為一個好剪接的可能性。如果你只是一直工作,沒有對自己要求,充其量你只是技術精進,心靈都沒有改變,這是非常非常危險。我們應該彼此共勉,對我來講,我就是會一直工作到掛掉為止,我每天都會比前一天更好一點、更努力一點。這沒辦法倚老賣老,為什麼?因為每個片子都是一個新的人,你都要重新面對,希望各位對影片採取平等對待、瞭解、陪伴,重要的是要讓影片告訴你它是誰,你一定要讓它自己告訴你,而不是你去切割它,那是你自己潛在的能力,你可以看穿它,但更重要的是讓它來告訴你,瞭解嗎?千萬不要當上帝,不要當檢察官,不要以為你可以超越它或處理它,應該要互相平等對待,去聆聽、感受得出來的東西。

【學員提問】
Q:剛剛有分享到說一個好剪接師要忘得快,假設我們在過程中一直做,不斷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還要用另外一個觀點持續去修,那要忘到什麼程度才停?
A:侯導現在還覺得《悲情城市》再剪會更好,到現在二十幾年了還在說,所以這個話我已經很習慣了。沒有經費就不要改了,因為改片子非常花錢,瞭解嗎?我跟侯導剪《紅氣球》,當初是我們拍了一個半月,但我們的女主角茱麗葉畢諾許拍了二十幾天,就要去美國拍好萊塢電影,所以侯導沒辦法補拍。侯導是有名的愛重拍、補拍,拍到老闆崩潰、監製崩潰為止,他沒辦法補拍,所以他回來就整我,剪了一年,剪到我快要憂鬱症。片子終於剪完了,上片前一個月,剪完放了三、四個月,終於要上片,還有一個月,侯導說我要再看一下。片子都印出來了,侯導說他要看,看完轉身跟我說「我要重改、重mi。」我們又花了五十萬。重改是需要成本的,你只要想到要花多少錢,想改的想法就會跟你說再見。如果你要留給自己記錄,如果不花錢,可以一直剪,剪到崩潰沒關係,就你自己的成長可以剪。但我不希望你因為這樣把自己陷入困境,尤其是你搞不定一直剪時會很崩潰,很崩潰時最好有朋友當你顧問。如果你不夠客觀,找幾個朋友用客觀觀點幫你看,是不是你做對了,也許他們對你再剪的版本不滿意,會大罵你是笨蛋。你一直剪,哪知道做對了嗎?找朋友來幫你看,找到客觀觀點,還是有人懂得你做了什麼,你才會進步,不然你就只是自己enjoy而已,這樣不太好。
Q:每次拿到新作品的素材時,你在第一次看時有哪些習慣?
A:因為我現在當剪接指導,比較沒有機會這樣看,但是我年輕時,至少把所有素材看三次,而且這三次是只看,不溝通,只有單向從影片過來的東西,講句術語叫「感受」,只能感受,不能交流。不能說:「喔,這女主角好美。啊,演得好爛喔。」不能批評,只能感受,而且如果有哪段胡思亂想,就倒回去重看。坐在那專注看三次,基本上是一種專注欣賞,就是你要很享受。可能有些拍得很爛,但希望你就是去看,NG就NG,你只能看不能想,有點像用影像在打坐,你都不用記,片子的好壞你都知道,而且很深刻地知道,比別人幫你看完,給你打勾勾來得有用。
年輕剪接師都用電腦剪,看完後就打勾勾、打點,剪片十個月都在這些點點勾勾上面,只看他們認為好的部分。我常常改他們片子,是把所有片子看完,直接改掉,比他們本來剪得還好,主要是他們沒有對影片的全面的概念。所以第一次一定要全面感受所有影像素材的好壞,一定要用感覺,而不是交流、對話、批評。我認識的名影評人,他永遠看片都要拿一張紙、一支筆在那邊寫。我說你跟我看片,可以不要拿紙筆嗎?我拿出我文青堅持的態度,結果他看了二十分鐘就喊停,說他沒拿筆不會看,馬上功虧一簣,又開始寫了。當你在寫字,你跟影片已經分離了,當你說好說壞時,你已經跟它斷絕關係了,斷絕全面相處的關係。只有在不批判、很專注地看,不管好壞、全心全意地面對時,但又不是像在看情人,情人又太專注、太愛了,不行。要用又不愛、又不恨,用很平衡的觀點去看,這時候你才能得到。專注看三次,不用密集看,可以看一看,休息一下再看。這專注的看,所有優缺點都知道,你很知道哪時候要用不同的替代,這其實才是剪接的開始,你瞭解你的對象,而且不是像神一樣去看,而是平等地、像面對朋友、很認真去看,而且腦袋不能轉來轉去,這件事很難做到,但這是成為好剪接的開始。
Q:剛剛提到很重要的「角色的情感邏輯」或「觀眾的情感邏輯」,是否可舉些例子解釋得更清楚?
A:當觀眾坐在那裡,他面對影片,影片在前面,當他看過去,他是透過哪一個人去看影片?中間有個人就是導演,觀眾是透過導演的傳達去看,這時候導演變成說故事的人,他用他的故事邏輯去影響你,可能有 1、2、3、4、5,只要有分鏡就在影響你,就在說他的故事,在這個情況下,觀眾是一個被動的人。
但我們有一個方法,幹麼我們要被導演影響,誰最大?觀眾最大。當我們把導演消失掉,觀眾面對的是影片本身,變成不須要「被說故事」,而是直接看影片的觀點,這時候觀眾讀到的是主觀的邏輯、主觀的情緒,當沒有人在中間時,觀眾變成感受的主體,你一定會問我「那怎麼做到呢?」你要把1、2、3、4、5弄不見,這個在文學上,你們應該知道很多,「詩化」有沒有?最簡單的「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枯藤老樹昏鴉」都是名詞跟名詞相接,就會有情境,他沒有告訴你枯藤上面站了一隻昏鴉,沒有連接詞跟介係詞,他只給你名詞跟影像。所以當導演把自己的邏輯語言去掉,影像就變成觀眾的主觀。譬如說1、2、3、4、5是順序給下來,人家就會follow,如果1跳11 ,11再跳30,邏輯不見的時候,觀眾就要自己讀了。因為你不給邏輯,當你的影像變成一張張照片而已,沒有邏輯穿插在中間,觀眾就變成主觀。其實這有個規律,冠詞、連結詞都去掉,只剩下名詞跟動詞,只剩下情境、情狀跟影像這樣而已。
仔細去看《悲情城市》, 事實上就是這樣,因為侯導不連接啊,我只能這樣跳著剪。我常常第一場跳第五場,第五場跳第八場,我要解讀的是觀眾能不能接受這個跳。本來辛樹芬到醫院,是先進去報到,再到宿舍去。沒有,我讓直接跳過去就是照片,她已經在宿舍跟梁朝偉講話,她已經到醫院了,中間的過程都沒有。為什麼這樣剪?因為侯導不拍啊,不拍你就要想辦法解決觀眾的感受問題,我剛好把囉唆的東西去掉,主觀就變成觀賞者,觀賞者最重要的一點,你要變成主觀的話,要去掉分鏡的邏輯,當觀眾面對影像,你要剪的就是觀眾感受的邏輯,這時候你可以進入詩化。像現在的快剪,剪到非常非常快,事實上也已經不是邏輯,因為你看不出邏輯。剪得很快、很緊湊,分鏡關係不是那麼清楚,而是情緒。你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它剪得更密一點,密到觀眾分不清楚邏輯,那也變成主觀。主觀、客觀主要在於觀眾的感受,還有觀眾感受的狀態跟內容是不是你要給他的。所以主觀邏輯很適合講那種老人、情感、反省的,面對以前的困境、回味……,那種東西都很適合剪觀眾主觀的邏輯。說故事的就好萊塢電影,就說故事說得很密集,但好萊塢現在有個狀態,他們把故事剪得非常密,密到都變成感覺了,也有可能用這個剪接的邏輯,可以創造觀眾投入的情境。
你去看《悲情城市》就會了解,當你跟它面對時,觀眾的主觀竟然跟影片會重疊在一起,當你用主觀讓觀眾跟影片重疊在一起,他對影像的感覺會非常非常深刻,所以他很適合講情感綿遠悠長的電影,感覺會非常浪漫。你去看安哲羅普洛斯,也是接近這樣。也有人很厲害,拍故事拍到讓你沒感覺,就像是拍《櫻桃的滋味》的阿巴斯,用簡單邏輯就能拍出超越的東西。但你別忘了,這導演著重的是人物、小孩,是真正人物的感情。像《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一直在跑,那多長的邏輯,跑來跑去跑了一晚上,但你看到的是對朋友誠摯的愛,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形式真的不是絕對,情感的表達才是要去注意的,傳達這個部分的情感才是你應該注意的,你到底要傳達人物的什麼?你到底要傳達故事的什麼?形式絕對不是最重要的,但總有一個形式來表達這個情感是最好的,這是你要去掌握的。
我也常常把導演設定的「情節邏輯」的東西,轉成「情感邏輯」,我就透過一個角色去剪。譬如我剪過《踏血尋梅》,原來郭富城在裡面是龍套,但我後來發現還原郭富城跟所有人的關係,那個影片就活過來了。我幫他加了四十分鐘的戲,郭富城就活過來了,他第一次拿到香港金像獎男主角。事實上你要注意的還是角色到底要傳達什麼、導演到底要做什麼,你要問清楚才知道。我記得我說兩天要幫他剪好,結果一放,看得我一身是汗,因為片子超級複雜,看得我都發傻了。後來我想清楚,好像還原郭富城,其他人都還原了,找到key point,他就是那條脊椎,我花了一天就剪完了。這不是在展現技術,而是你看事情有沒有看清楚,事實上看到問題的點才是最重要,你要一直問問題,至少要問導演或相關人員五個問題,問完你的答案就在裡面。你不要想答案,但你要會問問題:為什麼這樣?你到底要表達什麼?為什麼要給我這個?為什麼…五個為什麼,答案就出來。所以你不要去追求答案,要追求問問題,答案就在問題之中。也就是倒過來看,答案就在細節裡,就在執行的細節裡,是你們要去發現,要夠理性,夠感性才能判斷,要夠有經驗才能判斷。
Q:我相信導演都希望可以找到挑戰他、有主見,可以提供不同觀點的剪接師,但有時可能在性格或工作方式上會遇到一些比較緊張的時候,但又希望維持戰友的關係。在前期尋找團隊時,哪些問題可能是還沒有開始合作時可提出來確認雙方的?
A:你要找剪接,要先看對方工作過的片子,至少會在片子中展現他的個性,一定會,也讓彼此都瞭解彼此在做什麼。至於剪接的衝突,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讓導演醒過來,真的是這樣。我講我的經驗,剪接要怎麼調整自己,我在三十多歲時做了一次心理測驗,叫做思考人格,那有九種人格,什麼現實的、浪漫的一堆,有不同風格的人。你知道我的分數是什麼,我每一項分數都是第二名,畫到九個人格上面,我的思考是平的。為這件事我困惑半天,我還覺得我是變色龍。二十年後有一天我想通了,為什麼這麼平?我是被導演逼的。你從導演的角度來想剪接:我要一個剪接,第一個他要能幫我剪片子,第二個他又一定要跟我相契合,總不能導演要什麼,剪接都搖頭,你搖兩天頭就會被fire了。每個導演都希望有瞭解自己的剪接,真的是這樣,你們很想碰到一個剪接簡直就是soul mate。我跟你說,我很努力當每個導演的soul mate,這很現實啊。
我跟楊德昌聊二十分鐘,我就知道他的個性是什麼,我就會調整我的思路去跟他match。來個很浪漫的,我也調得很浪漫,所以調來調去我就變成變色龍。主要是要有同理心,你知道他要幹什麼,那你為什麼還要跟他唱反調。除非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你就可以不follow他。其實新浪潮的導演們,是我這輩子工作過最有肩膀的電影人,他們事實上很強烈地傳達自己對社會、對很多事情的觀點,而且堅持從頭到尾,沒有改變。如果現在楊德昌你跟他講,他還是爬起來跟你幹架,真的,我相信就是這樣。問題是我是剪接,我要跟他們工作,我不知不覺會把他們身上的東西印過來。我講我一個經驗,例如我坐到辦公室,我會突然感受到一個灰色的感覺在我身邊,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今天感覺這麼灰色,原來是公司有同事親人過世。你要把自己調整到可以吸情感,當導演坐在你旁邊,你就用情感穿透過去,就把他掃描了,馬上知道他的價值核心,跟他同步,他會enjoy跟你的工作。這不是你去討好他,是工作上你的需要,但不需要將就他。
像侯導剪不好,我就會一直跟他講改一下吧,每天就去煩他,煩到他說「你愛的話你就剪吧!」雖然他最後可能還是會剪掉,但你不放棄你跟他的溝通。但是最後最後,你雖然跟他那麼有默契,最後如果他堅持,就算你跟他講缺點了,他還堅持,事實上名字是掛他的,他願意去承受他留下來的創傷,或許以後是創傷,現在還不是,他願意承受這個,你應該讓他走他的版本。這就為什麼所有人都想當導演的理由:要表達自我。所以你看剪接又再次沒有自我,剪接是完成所有人,所以我的感覺是你要「無我」,沒有我的存在。我讓影片呈現所有工作人員在裡面最好的呈現,因為剪接本身太沒有工具色彩了,常常最後你是所有人踩在你身上拿獎的人,但是這個影片是因為你,所有人都拿獎,你應該要享受、高興這件事。他們可能以後沒有工作,但是你還繼續有,就完美了。重要的是我能繼續一直做,讓我能影響整個電影的環境,讓我能在裡面充滿創作的快樂。
每個片子對我來說都是新的人,每個片子都能讓我找到新的創作方式,讓我找到徹底解決這個片子的調性,讓片子變成活生生的人,傳達獨一無二的價值,當你影響很多人心靈上的感覺時,那是非常非常快樂。不只是商業,也不只是藝術,是你面對一個影像,做了一個最適當的傳達,讓它活靈活現地傳達出來,這個快樂絕對不是任何獎或任何稱讚可以取代,來自於內心自己對自己的肯定跟滿足,這才是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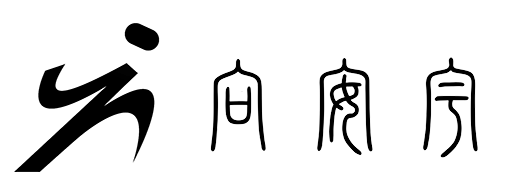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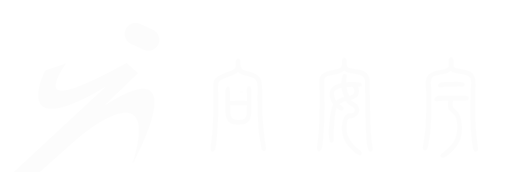
请登录以参与评论
现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