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里的妙玉说宝玉:
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时间的文化。
你看这吃茶,便有这许多功夫。功夫即时间,只有时间慢下来,才能琢磨出光阴的味道。
大概每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爱往乡村里跑。原本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是基于农业社会的土壤。没品味过乡村的生活,在钢筋水泥的牢笼里聊国学,对不起,我不想跟你聊。
宜昌是个小城,郊区村落众多,但好多地方都被“乡村旅游”所污染。一零年左右我跟好友淳鹏,特别爱跑谭家沟,吃顿农家饭,晒晒太阳,吹吹风,很是惬意。
大约一二年左右,跟几位朋友再去玩的时候,窄窄的乡间土路,挤满了小汽车,堵车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到了老谭家,可是各种水泥修建的平台、泳池像伤痕一样横亘在峡谷里,早已面目全非,那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南边村前前后后去过五六回,那里也在悄然变着。

南边村位于宜昌市黄花乡。那地方也曾是徒步的驴友们常去的地方。
大约是一二年,和黄烁老师一块儿去南边村,搭乘前往雾渡河的小巴,下车后徒步上山。在依山就势的石头路上攀登良久,近乎绝望之际,才遥遥看见树梢间翘起的鸱吻。

那时樱桃花盛开,油菜花遍地。青砖黛瓦掩映在黄色、粉色和翠绿之间,背景是峡谷对岸的白岩墨山,重峦叠翠,五彩错落,虫鸣鸟叫,鸡犬相闻,若再有溪流抱村,这大概就是大山里最完美的乡村了。


站在这样的乡村里,很容易想到陶渊明。
我在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农田和桑林里,一步步走到庙堂里,在入世和出世之间纠结着向前。而到了陶渊明,弃庙堂之高,也弃江湖之远,独守良田几亩,真是个异数。
木心讲课,说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塔尖。有人立刻问:那陶渊明呢?
木心答:陶渊明不在中国文学的塔内,他是中国文学的塔外人。
陶渊明之前没有陶渊明,陶渊明之后还是没有陶渊明。
中国的文化、文学,总离不开跟庙堂的眉来眼去。
但我也想跑到塔外,看看塔。

那一年的黄老师。当时他刚购置一台宾得单反,于是两人约着出门采风。
南边村易家老屋,加起来十六七个天井,围墙、角楼,壮丁的房子、下人的房子、牲畜的房子,大花园、小花园,前厅、二厅、主堂屋、围堂屋,秩序井然,规模宏大。
抗日战争时期傅正模于此设预备四师政治部,并办小学,内部结构基本全毁。文革时候又将几乎所有雕花毁掉。又有不少石材木材被当地百姓拆去盖了自家房子。年久失修后,在暴雨中后方靠山的墙体几乎全部坍塌。
几幢老屋,漫步其中已早不能想见当年的盛状。只能在某些边角,依稀看到当年的“奇技淫巧”。



老屋后面的老井。当年去的时候,泉水清凉,站在井口前,嗖嗖的凉风扑面。2017年再去时,特意去找过这口井,已是痕迹杳然。
当年前去老屋时候,大门紧锁,但刚好碰到有钥匙的乡民,于是得以进去屋内参观。
走在其间,仿佛从明清一下子跨越到建国后的某几十年。

雕刻精美的门,上面动物、人物,全部被挖去了头。乡民介绍是当年破四旧时毁去的。
推开门,墙上贴满裸女。

毁掉工匠们“如琢如磨”的技艺,替代以工业化批量生产的艳俗,推开嘎吱作响的清朝木门那一刻,看到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
如今我们依然干着同样的事情。
不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化,因循守旧大可不必。商朝遗民孔子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我们这个时代,不仅鉴于古代,更鉴于世界各国之文明,兴盛璀璨,远胜于前。
只是在吸收拿来之时,如何取舍,真是这一辈文化人应该努力的。
2017年,我和夏老师、淳老师再次来到易家老屋,门口已经树立起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现场的工人们正在重修老屋。

一水儿的水泥灰砖,水泥糊的墙和青砖墙、土墙格格不入,内里机器雕花的木门离精美相去甚远。

“老号”正面的墙上连窗子都消失了。我想如果将来有人要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研究明清古建筑,估计是一头雾水。说不定还要认为集木石建筑之大成的明清建筑师们,蠢到家了。
无论从风水格局、从采光和通风等角度,这面墙没窗子都说不通。为此我和友人争论良久,最后只好翻出几年前的照片为证:

“多、快、好、省”搞经济建设可以,做文化复建,还是费点功夫的好。
中国传统文化是时间的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观点是“逝者如斯”的河流,既是永恒流逝的,又是因果相循的一个整体。
赶得快了,就是湍流,有漩涡,有回水,危险的很。静静的流淌,才有平安喜乐。
到了易家老屋,再往山上走,有易家孙子辈修的屋,现在还住着人。
我和夏老师、淳老师,在这里找农户订了一顿中饭,然后坐在门槛上等饭熟。

这家有对胖墩墩的双胞胎,父母在外上班,放在老家给爷爷奶奶带。
我们刚去时候,双胞胎里的一个小胖子,裤子都没穿,跑来跑去。后来可能看到我们在拍照片,才去穿了个小裤衩。

门口的石鼓是双胞胎的“坐骑”。这里石鼓早残缺了,多年前被偷走了底下的石刻。
前几年去的时候,我还见着有一对立着的石鼓:

几年前和黄老师一起过去时候,还有一对立着的石鼓,这次去没见到了。

屋里的奶奶说,这对石鼓半夜被人偷走了。
我四五年前还在这对石鼓上坐过,当时拍的照片里,还能看到以前石鼓的样子。

我在用无人机俯拍天井。
数年前和黄老师在“老号”门口一家农户蹭饭吃,80块钱,一个小脸盆大小的锅,煮了一锅熏得半干的腊猪蹄,外加五六个荤菜,三四个素菜,两人吃撑,印象深刻。
这回我和夏老师、淳老师三个人,100块,干净的农家菜,味道不错。
双胞胎小胖子忙前忙后上菜。

这个老屋很大,一排几个门户,住了几家人,吃饭这家是其中一户。
几户人里,除了这对双胞胎,全是老人。

两个小家伙在玩王者荣耀。
我老家也在农村,周围所有村里,几乎都只剩下老人。
说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最先老的,是农村。
这里的生活不是“慢生活”,这里的生活是停止状态。

生活、文化这样宏大的命题,偶然想想就好,不必深究。
吃完饭,找个角落,沉沉睡上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三四点,打道回府。
下次再去,不知是怎生模样。
视频偷懒了,软件老崩,越剪越烦躁,放弃了……
而且拍得太零碎,组织不起来,也算是积攒经验了。
现在视频剪辑,节奏越来越快。信息越来越多,大家自然开始追求单位时间获取信息量最大化。
但是,我很喜欢慢节奏的剪辑。慢下来,才有充足的时间去感受。
当然剪辑这件事,既是面向大众的,又是内省的,本人新手上路,慢慢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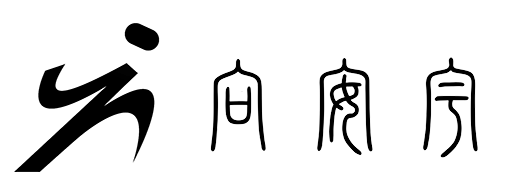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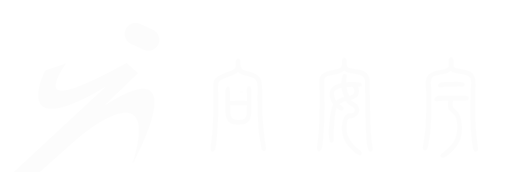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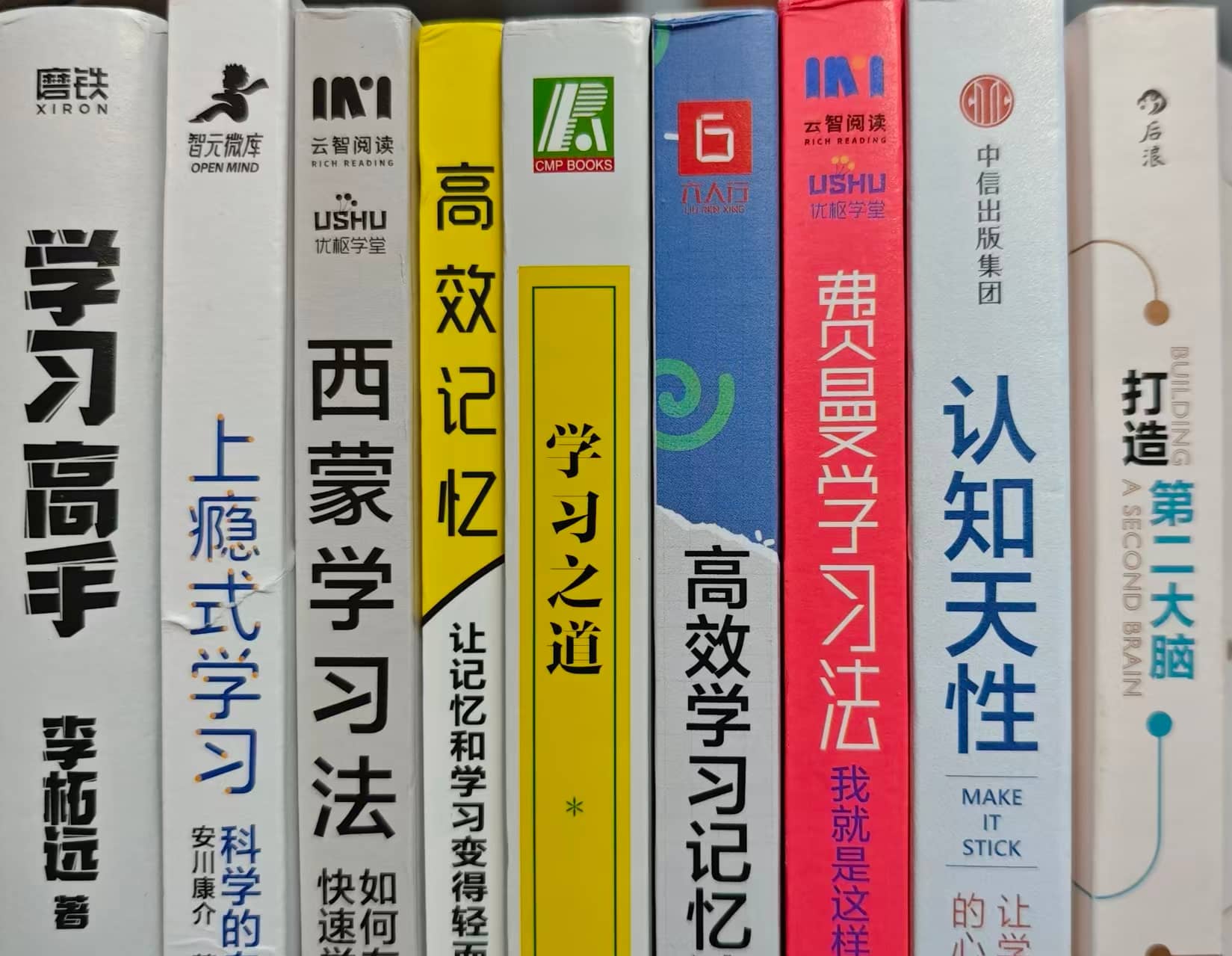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