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怎样提高剪辑的水平?
我想到我中学时代,那时候每次考试作文都是55分往上,甚至大型考试里拿满分。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平时作文,都去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套路,真正考试时候,平时积累的套路、方法、例子、语句,等等,都能信手拈来。
而真正开始决心好好磨练自己剪辑方面的能力之后,除开商业项目,我觉得平时那些试验片,更为重要。因为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实践自己的思考,而没有一个甲方需要去负责。
当然,试验过后,反思、总结,必不可少。所以,我才写这篇文章。
一、沉迷于章回体不能自拔
《哪边的年味》是我从09年接触单反后,就每年过年时候都拍一拍自己的亲人,一直拍了十来年了。
2020年,很特殊,离开武汉回家之时,所带行李,是只打算在家呆四五天的,没想到呆了两个多月。身上只带了一台bmpcc,一张硬盘。而以bmpcc 6k这数据怪兽的存储性能,一张2T硬盘真的是拍不了几个镜头。加上没有脚架等稳定设备,所以,最后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镜头。
怎样把没有主题的零碎镜头拼接起来,做成一个至少能一看的片子?
去年剪辑了一个记录长片《辟谷者》,被海量素材逼出了一个办法:章回体。
用一个个相对独立、有着各自主题、同时又互相联系的小章节来建构全片。
生活本身暧昧而复杂,影视作品只能尽力表现其一个横截面。但是现实主义作品,如果采用章回体,就有了另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多表现几个截面。
去年回家过年,疫情的影响下被迫隔离,又是第一个没有奶奶一起的年。一面要欢喜过大年,一面因为疫情前途未卜,一面要消化亲人离世的悲伤,一面要好好陪陪尚在世的老人,心情复杂。
过完年,忙着工作上的事情,也无暇去思考怎样把那些零碎镜头拼接起来。后来某天突然开悟,既然现实本身就是这样碎片化的、百感交集的、复杂多变的,为什么我非要从中提炼出主题,把复杂的本质变成单一的表象呢?
于是我放开了去剪辑,直接把零碎的镜头拼接在一起。这不就是这一年,我感受到的年味吗?
但是剪辑不是素材的堆砌,剪辑过程中,还是分开了几个部分:
画地为牢:疫情下的生活。虽然被隔离哪里都不能去,但乡下地方,影响不大,除开第一个7天,因为担心在武汉时候就已经被感染,有一些焦虑,然后就是在有限范围内的乡村生活。
阴阳两隔:怀念奶奶。
一生无恙:二佬佬和二奶奶。我记录了一些他们的生活,也听二佬佬讲了讲他的过往。
春暖花开:一切都会好的。
田园将芜:亲人们还是会分离,不能陪伴。
前阵子我把视频发给亲朋好友看过了,但某一天还是觉得不满意,又重新调整了章节的顺序。
大致上,这就是这一个春节了。
二、剪辑是时空的艺术
过年在家时候,拉了一个片子的剪辑,写了点东西,然后还被影视工业网推到了首页。

从不同渠道,总听到类似的话:
电影的主角永远是也只能是“空间”(戴锦华语)。
电影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不记得哪里看到的了)。
剪辑营造一个重新的时间和空间(周宇老师的指点)。
……
我一直对电影里的时间和空间似懂非懂,所以,尝试着更深入的理解,我把眼光投向剪辑的历史。从最开始的段落剪辑,到连续性剪辑,到古典剪辑,到蒙太奇……从德国的形式主义,到前苏联的形式主义,到法国新浪潮……等等,从对时间和空间再创作的角度,重新去理解剪辑的历史,收获颇多。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问题,怎样提高剪辑水平?了解剪辑的历史是必要的。
为什么各个电影节都偏爱对电影语言创新作出贡献的影片?因为要想对影视语言作出创新,实在太难了。
网上有各种教vlog剪辑、短视频剪辑、电影剪辑等等剪辑的,但是,那些技巧、方法,实际上,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电影短短一百多年历史,那些技巧、方法,却已经被开发得让后人难以走出新路了。
但是,知识没有高低,只有理解层次的不同,我们虽然非常难以开发出新的语言,但是对前人知识理解的深度上,从个人的角度,却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
所以,如何提高剪辑能力呢?
1、开发新的电影语言,这很难很难;
2、熟能生巧的不断练习前人的方法,就像沃尔特·默奇说的那样,学习剪辑就像学习跳舞,唯有不断地练习、练习、练习。
3、深入思考,提升自己对前人观念理解的层次。
剪辑《哪边的年味2020》时,我想到了如西德尼·吕美特在《当铺老板》一片中的手法。为了表现一个从纳粹集中营生还的中年犹太人,无法从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吕美特一开始用了几个回忆镜头插入现实时空中,而现在的事件和过去的事件很相似,意味着角色无法走出过去,而闪回的镜头越来越长,最终成为主导,角色摆脱过去痛苦记忆的努力也彻底失败。
在《哪边的年味2020》“阴阳两隔”这个章节,学习了吕美特的方法。
2020年打牌的镜头,中间闪回2017年奶奶在世时候观看妈妈打牌的镜头,并且闪回镜头逐渐变长,直至闪回镜头成为主角。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因为镜头数量的限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还是尽可能去展现我要的效果。
先是烟花的镜头,营造年味,接着切到2020年打牌的场景。和2017年打牌的镜头,我做了一些区分:
首先,调色的差别。2017年的镜头,全部都是低调的,明度的直方图没有超过50%,饱和和反差都压低了,鲜艳的颜色全部单选出来做了弱化。2020年的镜头,全部都是高调的,明度直方图全部在50%~100%,饱和和反差提高了,鲜艳的颜色,比如红色的桌子,做了强化处理。2017年的镜头,都偏冷调,做了偏向阴郁的风格化处理。2020年的镜头,风格则相对明快。
其次,声音设计的差别。人物对话的声音保留,但是做了弱化处理。然后,2020年的镜头,都配上了播报疫情的新闻联播的声音。2017年的镜头,也有电视的声音,但是是当时录下来的现场声音,是电视剧里的声音。2020年的镜头,都有烟花爆竹的声音,2017年的镜头则没有。2017年的镜头,隐隐传来的还有水烧开的声音,并且这个单调、乏味的声音,从一开始的若隐若现,到后面不断强化,直到镜头完全切换到回忆里,也就是2017年的镜头之后,在奶奶躺在沙发上睡着时候,随着镜头转焦,所有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水烧开的声音单调的回响。最后,才叠上背景音乐,把情绪稍微推一推。
通过打牌,穿越3年的时间,还是同一个空间,回到奶奶在世时候的一些生活场景:剁骨头,和妈妈一起做饭,和家人一起吃团年饭,祭奠爷爷……
这样剪辑,同时也是因为土家族对生命的看法:离去的人,会陪着在世的亲人一起生活。阴阳虽然两隔,但从未分离。
三、段落镜头的遗憾
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单调”的长镜头。现在的观众,大多数很难忍受缺少变化的镜头,所以剪辑师,一般在一个镜头传达的信息完成后,就急切地剪开了。而随着观众对视听语言接受能力越来越强,镜头也变得越来越短。
可是有些镜头,就是因为它够长,够“无聊”,才让人印象深刻甚至魂牵梦萦。比如《都灵之马》片头那个长达4分17秒的老马的镜头。我太喜欢了。

这个以庞大电影工业体系作为支撑,才能够拍出来的镜头,其内容,只有一匹老马在荧幕上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没有其他的了。
普通观众多数是不能接受《都灵之马》里的长镜头的,但是,欣赏的人自然懂得欣赏。
《都灵之马》里面还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是两个人坐在桌子上吃土豆。镜头和演员没有任何调度,固定的镜头顽固地凝视着两个人慢慢地吃土豆。
后来我看到类似的镜头,金行征导演的《消失在黎明前》,一个村子剩下最后一个留守老人,老人做了简单的饭菜,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镜头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看着老人把饭菜吃完。老人的那种孤独,生命的那种张力,生活的那种无奈……太多东西融入到里面了。
这样的段落镜头,没有镜头运动,没有演员调度,但却是属于电影的独特魅力,如油画般呈现出的这个生活中的真实时刻,会击中观众心中某个平时无法触及的角落。
其实在《哪边的年味2020》最初的版本里,我把奶奶剁骨头的镜头,留的很长很长。我希望通过这个镜头,去展现奶奶平时的生活状态。爷爷去世后,奶奶多数时候都是独居,即使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她也经常独自一个人呆在那个因为熏肉熏得很黑的老房子里。镜头里,奶奶缓慢又坚定、努力又笨拙地把一块块肉剁碎,像《老人与海》里那个独自和大海战斗的老人一样,无声地对抗着岁月。
但是,当我决定把《哪边的年味2020》不再存档独享,而是分享给亲戚们之后,我把这个镜头剪短了。
不过,懂得人依然懂,一位朋友,在看完之后打电话给我,特别提到了这个镜头,说对他触动很大。
这也是做视频的乐趣,隔着摄影机、剪辑台,隔着网络、电脑、手机,和观看的人述说、沟通、交流。
四、声音:景别的节奏
电影一般也是过滤杂音,某些杂音可以建立环境的背景意义,而一旦背景与主角的关系清楚后,杂音即可消掉。
——《认识电影》
奶奶剁骨头的这个长镜头的声音,我尝试了一些设计:
- 进入屋子的镜头,声音是雷声和大雨的声音,这些都是加上去的声音,真实时空里是没有下雨的,用这些雷雨声烘托气氛,定下这个场景的调子;
- 镜头切换到奶奶后,雷声没有了,还有雨声,而且雨声弱了很多;
- 插入了犬吠,有大狗的声音,还有小狗应和的声音,前几声较明显,后面也弱化了;
- 剁骨头的声音始终清晰,其响度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电平值在-10~-5之间;
- 原本同期声有电视的声音,全部弱化掉了;
- 背景里的雨声、狗叫声等等,都在剁骨头的过程中渐渐弱化掉了,只剩下单调的剁骨头的声音在继续;
- 没有用任何背景音乐,任何音乐放这里都觉得太吵杂了。
这段声音设计,我是按照镜头景别的节奏感去做的。
对于镜头来说,是比较常规的设计:大全景交代环境,接中景,再接特写。
声音也按照这个节奏来设计:先是雷雨交加、狗吠阵阵,然后剁骨头的声音响起来,这相当于一个定场镜头:雷雨交加的夜晚孤独地剁骨头。这也是建立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同时渲染了氛围。
然后这些环境音被弱化,相当于中焦焦段。注意力集中到人物身上。
最后除开剁骨头之外的所有声音,全部消失了,相当于特写。注意力集中到人物正在做的事情上。
通过这种声音的景别变化,来把观众注意力集中到剁骨头这件事情上。就像是“月东出,雁南飞,谁家夜捣衣。”在一片景象中,独独一个声音的孤独回响,最易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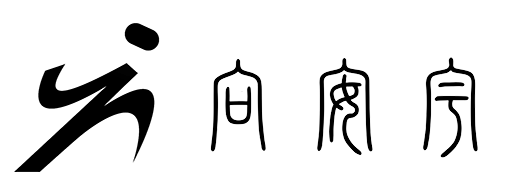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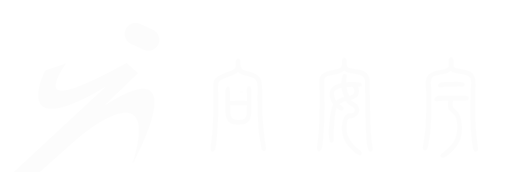
请登录以参与评论
现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