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显得相当的厚颜无耻。因为我并非知名影视人,没有人会关心我的历史。
更加厚颜无耻的是,我也算不上一个“迷影人”。“迷影人”在香港称之为“影痴”,说的是对电影痴迷的一帮子人。我顶多算半个。
也许当我成名之后,我会标榜自己从小与电影结缘,甚至于将观影史上溯到在娘胎时到胎教。然而现在,我还是老老实实写点实话吧。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电影看了。一年至少有一回,村里的大会堂会有一次电影放映。
每年那个时间,村里干部走乡串户提前通知,当天十里八乡地村民提着自家椅子和板凳,走上十几里山路,汇聚到村里的大会堂。
说是大会堂,其实也就比一般教室大一点点。那是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土屋,泥土垒起来的墙,窗子是几张薄膜钉在木框上,站在屋里抬头就是房梁和黑色的瓦。后来为了保证采光,用了几片亮瓦,就是一种透明的瓦。
虽然屋子小位置少,但少有闲人会提前去抢位置的。白天都要干活,到了下午才三三两两地过去。我们家过去时候,一般连屋子外地窗口都已经被占领。小孩子挤不过大人,但是幸好村里的几个大孩子够意思,经常会把我接到房梁上。门口是早就进不去了的,我要被人抱着从窗子口塞进去,然后从大人的肩膀上、头顶上爬向房梁,再由上面的人拉上去。亮瓦底下的房梁,无异于大剧场二楼的VIP包房。
然后就是等,大人们嗑着瓜子聊着家常等,小孩子窜上窜下哇哇大叫,等到天黑时电影正式开始。大家安静看完,散场后各自拿出沙树皮制作的火把,扛着椅子板凳摸着山路各自回家。也有手电筒,但是少。那个年头,需要金钱购买的电池,远不如山上随处可采集的沙树皮经济,所以手电筒只是火把携带不便时候的备选。但是看电影携家带口准备充分,沙皮火把也备好了的。所以散场后,常常有红军长征夜晚行军的即视感。
再后来,有了露天电影看,地点在岩板井小学的操场。把一块黑边白底的幕布,绑在在二层楼的栏杆上,底下绑上几块石头固定,远处支个桌子安放电影机。那时候,身为小屁孩儿,最感兴趣的是跑到幕布后面看反过来的电影,比在正面看电影的观众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回想起来,看过的电影一部都记不住。
倒是记得几部再后来才出现的录像带。
录像带并不是随便就有看的。一般是哪家办喜事,会请一台录像机回去,录像放映员一般还要带电视机过去。
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大决战三部曲。还有就是一部“吃辣椒的”,后来知道那是成龙的《A计划续集》,那时候记不到名字,就记得里面主角吃辣椒快被辣死的镜头,所以将这部电影称之为——“吃辣椒的”。之后还有《快餐车》、《碧血剑》、《霸王花》等等,哪一家办喜事,记住的只有电影。对了,还有一次小学组织放的录像带《闪闪的红星》,在那个二楼顶头的一间教室,白天糊上窗户放映的。后来每一次小伙伴一起玩时,扮演大坏蛋的家伙返场时必须喊一句话——“我胡汉山又回来啦”,然后一边抖肩膀一边狞笑:“嘿嘿嘿嘿嘿……”。
印象深的还有一部。是在春树淌(地名)的一家人过事,放了一个电影,诡异的魔幻风格的都市时装片。回来后在门口小卖铺里,我哥和波子叔叔聚在一起讨论。
两人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那个片子咋样?”
“有点黄。”
“嘿嘿,我也觉得有点儿。”
“嗯,嘿嘿。”
“嘿嘿。”
那种神秘莫测的笑容我很多年后才懂。后来偶然间居然再次看到那部电影,其实也只不过有几个接吻的镜头而已。
小时候屋里有一台电视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记忆里一开始就存在。那是一台panda的彩色电视机,厚实的实木壳子,看着像一个沉默不语的树墩子。而事实上,很多年的时间里,它也一直是沉默不语的。
那应该是村里最早的一台电视,是台湾的亲戚买回来的,不过在他的料想之外的是:山里没有信号,以至于这台电视很多年都呆在专为它打造的柜子里吃灰。
印象里这电视第一次亮起,就是租来录象机放电影。放的就是淮海战役,空中俯拍的行军镜头印象深刻。
后来村里开始有了其他电视,然后几个信号点也被开发出来。大山隔绝了电视信号,只有在几个特殊的地点,会有从山凹凹的缝隙里漏过来的信号。这些点很难找,需要扛着两三米高的木杆,架着天线四处搜寻。
那时候,朱家屋场的那半边山有电视信号。于是那台panda的电视机,就被搬到了我父母工作的岩板井小学,一排教室顶头上的那间办公室,也是最靠近那半边山的房间里。然后天线接到屋外面,尽可能靠近朱家屋场的方向。
我最初的观影体验里,看电视就不是一件家人在一起的私密事儿,而是乡里乡亲的聚会。
办公室白天要发挥学校办公场所的作用,到了晚上,家里人、亲戚、附近的村民打着火把和电筒来到学校,和住在学校的老师们一起看电视。
接收电视信号的天线特别巨大,一种很轻的金属管道,圈圈绕绕地盘在一起。天线还很傲娇地必须被架设得尽可能高,并且还必须以某种特殊的角度伸向空中某个非常精密的坐标点,稍微差一点就没有了信号。但是为了那一点点从山凹漏过来的信号,天线必须安放在正对着山凹的地方,所以也必须接受山风的考验。
还有就是,信号不是固定的,会变化。每隔一段日子,那个存在于虚空中的、有信号的神秘的坐标点就会发生偏移。然后天线就需要挪位置。
正因为如此,这个天线不能完全地固定死,要能够让人搬得动,但又不能让风搬得动。当只有木杆和铁丝这类工具的时候,这就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人,和风、木杆、铁丝、天线、以及神秘坐标点的来回拉扯。
理所当然的,电视信号习惯性消失。
于是,经常在电视剧进行到精彩的地方时,一阵妖风吹过,电视只剩雪花飞舞。
这时候我爸就得出去,搬上梯子,去屋外微调天线的角度和位置。
我爸在屋外全凭感觉摇动天线,一边喊:“好了没有?”
屋里人应声:“没有?”
我爸在屋外继续:“好了没有?”
屋里人回:“雪花少点儿了。”
我爸就很高兴:“这会儿呢?”
屋里人答:“哎呀,又没了。”
这样来回反复。
运气好,几分钟就好了。运气差,得折腾几个小时,甚至于赶上信号点漂移,这晚上都不用看了,得等到白天了,再次扛着架着天线的两三米的木杆,四处寻找信号。
那时候看电视,虽然节目不多,但是可以聊的有很多,一方面需要推理漏掉的情节,一方面可以和当晚没有失去信号的人家印证情节发展。
那时候,看的是《七侠五义》、《白眉大侠》、《甘十九妹》,到现在依然会唱里头的主题曲。
直到买了卫星锅(卫星接收器),这台panda才搬回家里。某天正在学校玩耍,看到在城里买的卫星锅倒扣在客车顶上被拖回来,兴奋的当时就想翘课回家,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回家后恨不得在锅里打滚。那时候的卫星锅是超大的,有两米多宽,后来这个锅在我家使用了近20年。
小学四年级,我爸工作调动,去了镇上。住在爷爷在政府大院的房子里,有一台黑白的panda。不接有线,只有央视一台和山东电视台,接了有线多一些台。但最多12个,那种电视是旋钮转台的,最多也就12个台。
那时候看过的经典应该是《新白娘子传奇》,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小侠龙旋风》。
这部电视剧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在那时候留下深刻记忆,并在将来的日子里成为我对待爱情的“往昔之井”。那个故事里有一对恋人,万里云和花舞影。两人被魔教女王花弄月下了诅咒,万里云白天是人形,晚上会被诅咒化作蝙蝠;花舞影夜晚是人形,白天却会被诅咒化成石像。两人相恋至深,却永难相见。同时还要应付魔教的各种危机。
漆黑的夜里,花舞影倚窗独对寒夜,万里云化作蝙蝠环绕左右;喧闹的白天,万里云守护着石像,四处辗转。
这差不多算得上是感情的启蒙,从此倾慕那种百折千回始终如一的爱情。
镇子上的中学,每周都有露天电影放映,一次两部,一部是爱国题材的,另一部每次不同类型,但都是国产片。
有一面专有的墙挂幕布。我靠着舅舅和叔叔是中学老师的关系,经常能挤到前排。但是很多时候,是和小伙伴一起爬到篮球架或者双杠上面看的。
虽然那时候看了很多,到那时说实话很多电影质量并不高,如今也记不得什么了。
再后来镇上开始有VCD,在政府大门侧面开餐厅的小伙伴家里看了很多喜剧电影,以及很多僵尸片,记得的有周星驰的《百变星君》,林正英的僵尸系列。
那时候镇上有了录像厅,说是录像厅,但已经放的是VCD而不是录像带了。有回凯凯哥哥从学校翘课溜出来,街上碰到我了,带着我去录像厅看录像。录像厅里外两间房,外面一间房对着门摆着一张铺板(哪种用来铺床的板子,一张板子半张床的大小),上面摆满VCD,墙上钉着木条,然后平行方向拉着松紧带,把VCD固定在墙上,整整三面墙的VCD。一进门,就有一种被电影包围的震撼。
里面就是间小黑屋。用很厚的布帘子和外间隔开。进屋就是一圈椅子,前面小桌子上面一个电视机,除此以外啥也没有。
录像厅一般是放什么你就看什么,但是先到的人有优先选择权。因为凯凯哥是翘课出来的,正是上午录像厅很冷清的时候,于是我们在外间慢慢挑碟子。
挑碟子唯一的参考就是蝶面上的海报和背后数百字的简介,而且盗版碟居多,常常文不对题,外面的介绍跟里面的内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想看好片子只能靠运气,再有就是靠口碑。挑花眼之后还是不知道看什么好。这时候凯凯哥拿起一张VCD:“看这个吧,这个我看过,还不错。”
然后我们就看了那个片子——李连杰的《黑侠》。一部画面暗黑,充满暴力的片子,在录像厅的小黑屋里,尤其地惊心动魄。
后来拿出压岁钱,逼着爸妈补贴剩下的钱,在县城买了台VCD机回来。比这我哥家里的型号买的,700多,在当时算是不少的钱了。
租碟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十块钱押金,一块钱一天。小伙伴组成帮扶小队,轮流出租金,大家一起看,有些好碟互通有无、一起分享。
然后《古惑仔》、《风云》、《哈利波特》、还有什么《流星雨》、《蓝色生死恋》等等,不管好片坏片,以几乎一天一部电影把租碟店子里的所有碟扫光,然后隔段时间去问:“老板,有新片子吗?”
初中时候,知道了“黄碟”这种事物。第一次看到实在我哥家里,白天趁大人出门,把门反锁,窗帘拉得密不透风,小心翼翼把声音调小,一边看,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旁边准备好别的碟,随时准备替换。
之后就开始搜集这种碟子了。镇子小,租碟子的店子只有两家。张华子的店是常去的,虽然跟老板熟,也不好意思问他要。张华子虽然是生意人,但是也不毒害我们这些初中生。所以“黄碟”的来源一是小伙伴分享,二是……偶尔会有包装简介和内容严重不符合的盗版碟,租回来的武侠片,打几下就上床了。现在想来应该是港台三级片,那时候盗版横行,片源乱七八糟的。其中就有一部讲蛇怪的片子,充满了蟒蛇、裸女、性爱的画面,成为了那时候的梦魇。
上高中以后,除了极少的学校组织或班级组织的看电影以外。看电影主要靠包夜。
包夜就是在网吧通宵,10块钱一晚上。上半夜玩游戏,下半夜累了不玩了,但花了钱包夜不能浪费,就看电影。我也经常会不玩游戏,刷一整晚的电影。那时候网吧电影是靠老板下载下来,然后文件共享的。所以每个网吧电影内容不同。至少方圆十里内,包括那些旮旯里的黑网吧,都被我看遍了。
那时候还有些口耳相传的特殊网吧,坐很远的公交车过去。上半夜跟一般网吧没啥区别,过了12点,网吧老板打开共享,各类小电影就可以任君观看了。于是会出现很好玩的一幕,12点刚过,玩传奇私服的一帮各色人等,整齐地退出游戏,点开小电影,都心照不宣也就不会放小窗口偷偷摸摸,都是全屏观看。有回在一个网吧里,房间是那种狭长型的,电脑整齐地排成很长的一排,我上完厕所回来,从这头走到那头,阅尽各种玉体横陈。
学校封闭式管理,去网吧毕竟机会难得,但是看电影还有另一个渠道。
教室里有一台用来每天看新闻联播的电视机,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些家离得远不得不留校的学生,就在教室写作业看电视。有一个点播频道,守在电视机前,等有钱的土豪点播,跟着一起看。
还有第三个渠道。那也算是我第一份与电影相关的职位了。
高中在市里,一周只休周日的上半天,很多来自县市的同学在周末都是留校的。我因为跟教务处管学生工作的刘主任相熟,被委任了一份工作:负责周末影院。
周末影院,就是每周六晚上,在办公楼负一楼的一个大厅,给留校的县市学生放电影。
放的电影有时候刘主任给准备好,有时候是我自己出去租。一般要提前确定下来,然后我还要在教学楼一楼的黑板上,以及去食堂的走廊上,贴出自己设计的海报。内容无非是一段电影的简短介绍,号召大家来看之类的。
那时候无师自通成为了一名标题党文案。
因为负一楼有一个健身房,所以那时候一般放学后吃了饭,就提前过去,健身房玩一会儿,在开门放电影,放完电影留在后面关灯锁门。
那时候看的电影就不再是来者不拒乱看了。而是看了很多世界上的经典电影。
高中时候还没有想过拍电影,那时候参加了一个学校组织的ps大赛,得了最高的一等奖,然后就膨胀了。看是研究图片,继而喜欢摄影,想把摄影当成一辈子的兴趣爱好。参加了学校的摄影兴趣小组,数码相机那时候还是贵得买不起的东西,手上只有一个用胶卷的傻瓜相机。拍了不少,好多都没洗出来就弄丢了胶卷。
上大学后有了一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看电影机会就更多了。在电脑硬盘还只有40G、80G这种容量的时候,我已经在以TB为单位删除看过的电影了。
华师有几个ftp空间,有几个是下面学院自己的,还有一个学校的,对内网是开放的,用于学校内部的文件分享。我负责打理的是学校的一个ftp空间,100T空间,上面全部是电影。我们用给TXT文件重命名的方式在上面交流,不断更新上面的电影。
大家都有上传的权限,但是只有管理员有移动和删除的权限。我干的活儿就是,不断删电影和号召大家上传新电影。同时,就是几乎上面所有电影都看一遍,也避免不了按自己喜好删掉一些电影。最爽的就是每学期末的大清理,几十个T刷刷刷删掉,看着进度条就想:“都看过了啊!”
然后下个学期,又在上面喊:“大家有什么好电影啊?”
也是那个时候看电影最喜欢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看。到现在,买书时候一个作者必须买一整套,一个导演电影必须全部收藏,一个电影系列必须全部收齐,少一部宁愿整部全部删掉。这种强迫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大学时候看过的电影真的是数不清了。那时候也写过剧本,拍过短片,参加大学生微电影节,都不成气候。后来也打算过报考影视文学研究生,也中途放弃。
工作后,有几年是文艺青年。那时候没事就到“恋爱的犀牛”咖啡馆看电影,朋友西瓜的店子,显示器摆的有点儿高,经常几个人仰着脖子看电影看到半夜。那段时间,看的几乎都是文艺片。
也是工作有收入之后,才开始经常去影院。那时候一个人,没女友,所以常常是一个人,去影院也是纯粹地享受电影。偶尔也和朋友去,但总觉得不如一个人来得自在,因为一个人可以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里。让整个世界,只剩下电影和我。
再后来,不再当教书先生。辗转了几分工作,来到影视行业。
当时改了QQ签名:“回到最初的梦想。”
两三年过去,策划、文案、编剧、导演、摄影、灯光、录音、剪辑、包装,好像除了制片和推广发行,一个片子下来几乎所有的重点工作都做过。
然而,没啥成就。
如今我依然只认为自己算不上“影视人”,也只能算半个“迷影人”。
说梦想,其实最初吸引我的只是广告片。双学位也是文学和营销,想去做文化传播。如今兜兜转转,自己都快迷失了。
前路依旧漫漫,更懂那些爱着我的人,也知道某些我爱着的人不可辜负。然而如今似乎我能够做好,并唯一会做的,就是视频制作了,是梦想之基石,也是谋生之手段。
所以,红尘万丈,唯爱人与电影不可相负。
尘缘万千,止存一心。忧之,惜之,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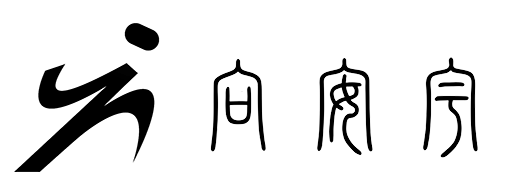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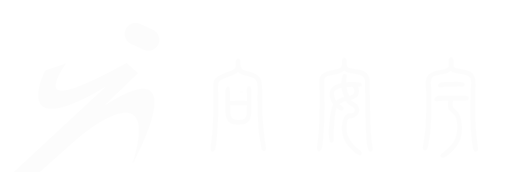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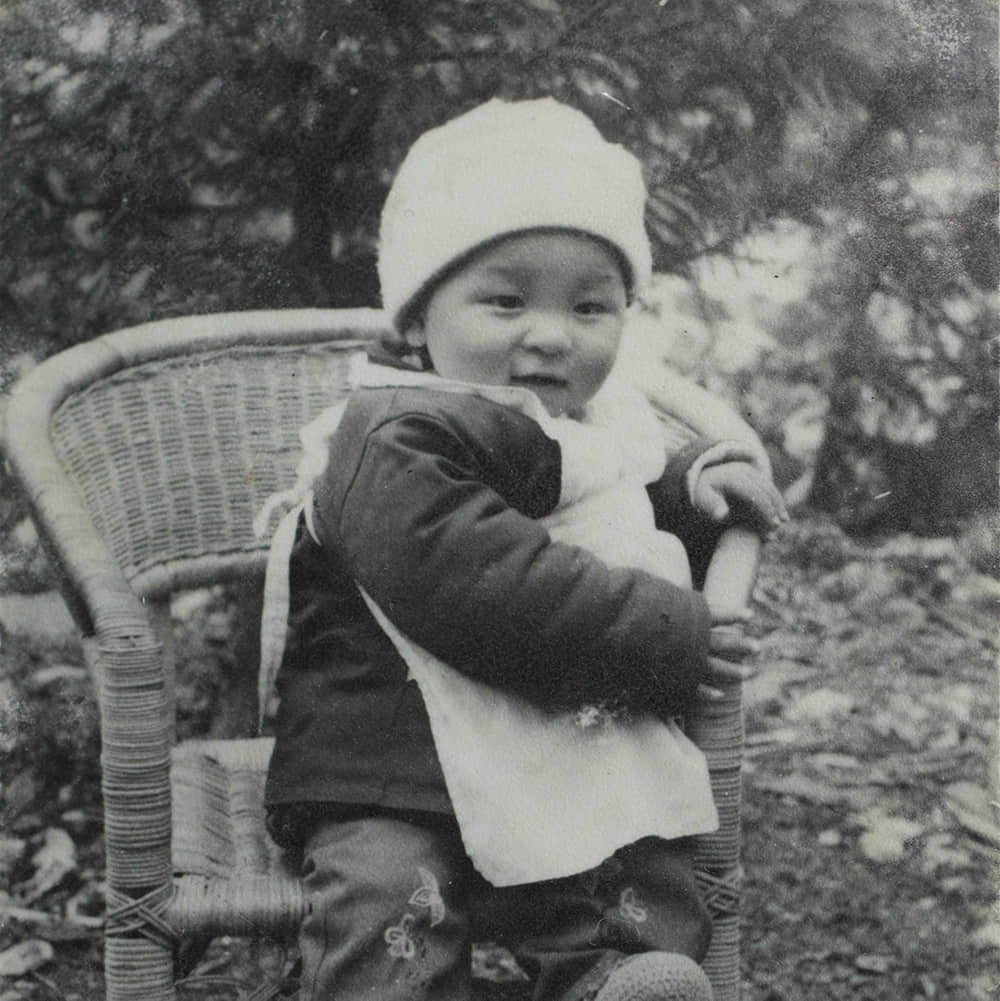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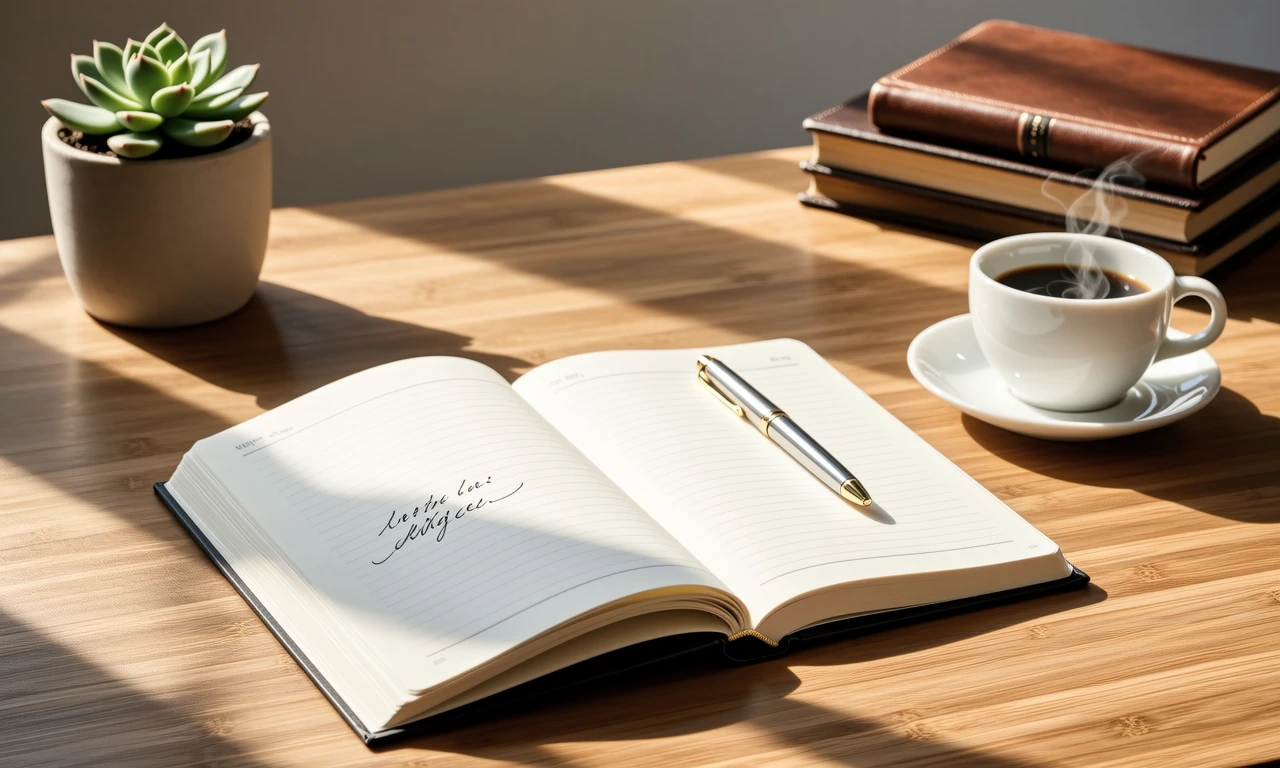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