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是记录一些自己的思考,思维跳跃,没有章法,介意者请绕行。
纪录片的创作是很有意思的,用脚创作多过用笔创作,大多数的案头工作是在路上完成的。因而,对于创作者而言,积累“方法论”是必要的。
前阵子有前辈发来一部短片,时下才得暇观看,发现这个片子在常见的套路里,融进了一些创作者的新意,使得“俗”套路瓶子,装了点新酒,有了不同的口感,变得有趣,于是决定拉一拉这部片子。
点击跳转至观看页面One Day in Life,这是人物塑造常见的手法,《72岁的一个晚上》用的就是这种套路。下面来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聊一聊。
1、一镜到底的开场,关于真实和事实:
第一个镜头,不是真实的现场跟拍,而是设计好的镜头。关于纪录片能不能排演的问题,纪录片届争论由来已久。我不是纪录片学者,不关心学术争论,我的观点是:纪录片可以排演摆拍,毕竟标志着纪录片诞生的第一部影片《北方的纳努克》就是排演。
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环境是很有意思的,在纪录片电影节上,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个词的前缀和后缀都有文献的含义)一定是有文献价值的,一定是反应现实社会问题的。但是国内“纪录”和“记录”是含混的,还有很多原本是电视台里做节目的人,以做节目的方法在做”纪录片”,甚至追求娱乐性,以愉悦观众,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制作的初衷。
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家庭相册,还有人在坚守这为这个时代留下影像,但永远是小众。
回到排演的问题上来,做“节目”全程排演当然都是可以的。我发现现在很多所谓纪录片,排演的成分越来越多,而观众也接受这一点,当然,很多观众根本分不清是不是排演。但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
排演,当然可以,但是要有度。纪录片的审美,就是真实,离开了真实,纪录片一无是处。
原则一:排演,要让观众看出来是在排演。比如有些无法拍摄到的画面,用表演复现是可以的,但是有责任的创作者一定会通过镜头语言明确告诉观众:这是摆拍,是“假”的。
《72岁的一个晚上》第一个镜头,一个一镜到底,跟着邱必昌去酒吧喝酒聚会。人物的出场,镜头的调度,人物的台词和走位,看的出来明显的调度痕迹,所以应该是排演过的镜头。但是这种排演,一般的观众是看不出来的,摄影刻意用了肩扛镜头,镜头的晃动增加了现场感,看似真实拍摄。不过也许无伤大雅,因为也许邱必昌平时去酒吧聚会就是这种状态。但是,也许不是,因为这是摆拍,有导演的创作,也有被记录者的意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导演眼中的邱必昌,或者邱必昌自己眼中的邱必昌,而真实的邱必昌是怎样的?这个片子给不了答案。

所以,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看到第一个镜头,我就直接关闭了页面,因为不再感兴趣了。我对“美化”的邱必昌没有兴趣,因为我会想:这是不是一部个人形象片?这是不是导演想要塑造的自己向往的一种生活?我没有兴趣去了解这样一个塑造出来的人,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人。
当然,现在很多人不再关心真实。给观众一个梦做,比向他揭露撕开伪装的现实,更能取悦观众。也就更能获得大众认可,更能收获名气和利益。这是创作者的取舍,不讨论。
宕开一笔,现在电子稳定器的普及,也影响到纪录片的审美。过往的纪录片,手持拍摄是标志,不稳定的镜头增加了临场感,我们接受这种不规则晃动有可能带来生理上眩晕的不舒适,因为我们认为真实大于一切。但是随着电子稳定器的普及,和小型摄影设备的普及,我们开始不再接受手持镜头的晃动感。
以往我们可以接受镜头的晃动。同时,我们认为这样的镜头更为真实。因为那时候,要获得稳定的运动镜头,需要滑轨、需要大炮,需要摄影组和机械组的努力,需要镜头调度和演员调度的通力配合。所以,这种稳定的运动镜头在纪录片里,会被认为是排演和摆拍,是不真实的。
而现在,随着小型电子稳定器的普及,小型拍摄设备自动跟焦的发展,改变了观众的审美。通常,哪怕是瞬息万变的现场跟拍,熟练的摄影师,也能够获得良好的稳定的画面。观众看到稳定的镜头,不会怀疑这是不是真实的现场抓拍。我觉得,这也给现在的纪录片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那就是:获得稳定的画面。
以往那种手持走天下的拍摄方式,不会再获得年轻观众的认可了。这是趋势。
回到《72岁的一个晚上》,第一个镜头,特意采用了手持镜头的背跟,同时手动跟焦多次虚焦,有趣,但出戏。
夜景,大光圈浅景深,不是机器自动跟焦的抽吸感,而是跟焦员稳准的跟焦,这个跟焦员已经相当厉害了,厉害到让我特别注意到跟焦员的存在。
原则二:炫技镜头留给不重要的过场镜头或者环境镜头,不要在关键镜头上去炫技。
炫技镜头,因为其高失败率的特殊性,需要排演。纪录片里炫技,可以有,不能多。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叙事里不被干扰,是创作者的良心。
但创作者要生存,指着情怀是活不下去的。而且我认为情怀绝对成就不了伟大,因为情怀有可以活,没有也可以活。但是商业不同,因为那是你耐以谋生的手段,有,活,没有,就没发活,休戚相关,关乎性命。所以,以做商业的目的来做纪录片,才是真正的拼上了性命,才能出好片。(是否向大众审美妥协,是另一层次的考量。)
一些炫技的镜头,能让受众群里特殊的一小部分:资方、甲方爸爸、合作伙伴……注意到这个制作团队,从而带来商业订单的可能。
总之,排演可以被接受,但是要有度。
回到《72岁的一个晚上》的第一个镜头。
首先,邱必昌进入一个酒馆。
曾经和NHK合作拍摄,那时候拍摄了一个跟随人物走进市场的镜头,日方很喜欢。NHK拍摄纪录片很喜欢提前开机,记录下进入那个环境时候的状态。只要观察人物和空间的关系,人物和他的环境的关系,就能迅速了解这个人物,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叙事。
接着,花白头发的邱必昌和一桌年轻人打招呼,交代出邱必昌是常客,且和年轻人关系良好。
这个酒馆是属于年轻人的,邱必昌人虽老,心态却年轻,这是导演在第一个镜头里就要呈现给观众的。(看这个镜头的运镜和焦点转换,这是一个经过排演的精确调度)
再下来,邱必昌和朋友打招呼,这个朋友后面也有出境。
有意思的是,这里邱必昌直接对着镜头,往旁边一指:“我们坐那儿。”然后带着摄影机来到聚会的朋友一桌。而邱必昌的朋友也直接对着镜头说:“坐,新朋友,来,坐。”
直接打破第四面墙,和观众对话,带着观众进入场景,很有趣。
这里其实还可以展开讨论到另外一个纪录片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讨论的问题。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因为纳努克一家一直在以极高的热情配合纪录片拍摄,一直没有储备足够过冬的食物,最后被饿死。制作者能不能介入被拍摄者的生活,也就一直被讨论至今。
而《72岁的一个晚上》,则在第一个镜头里,直接打破第四面墙,让拍摄者直接进入到被拍摄者的场景里。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72岁的一个晚上》挺有趣。第一个镜头里,就给出了自纪录片诞生以来一直讨论至今的两个问题的答案——导演自己的答案。
而这个片子是不是属于Documentary呢?或者,这应该算是一部人物形象片?抑或是一部宣传片?
这个镜头还没有结束,邱必昌去拿红酒,邱必昌的朋友接着对着镜头介绍:这个地方和老邱常来,听听爵士乐(镜头同时给到爵士乐表演的舞台),环境不错,老邱一定会去拿他喜欢的红酒……
一股油腻的玛丽苏的酸臭味。所以第一次看这个片子,到这里我已经被劝退了。
这里拉片,仅仅是为了学习一下人物短片的套路。因为自己近两年一直关注纪录片,所以一开始就从纪录片的角度来审视《72岁的一个晚上》,这个进入的角度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
不过,近些年好多这种片子,被称为“人物纪录片”。所以,以纪录片的角度来思考,也不算错。
而且大的趋势,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近些年越来越模糊。不仅仅是纪录片剪辑师在使用剧情片的叙事方法来剪辑纪录片,纪录片现场拍摄时候也有导演的调度。观众越来越关注故事,而非真实。
而从另一个层面,真实不等于事实。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叙事的真实,通常被认为高于事实。因为文学和电影,是艺术创作,不是新闻报道。
但是,我依旧固执的认为。纪录片虽然要向剧情片学习,但是绝不能丢弃自身最大的魅力:关于真实的审美。
让观众相信,他所看到的镜头前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人,而非表演,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切的经历,而非编剧的杜撰。让真实,以巨大无匹的力量,直击人心。以现实作为画笔来创作,这是纪录片独有的魅力。
2、给人物贴标签
第二个镜头,同样打破第四面墙,邱必昌招呼摄影机坐下,别客气。接着说: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喜欢玩,从小就皮”。
接着就是一组玩水上摩托等项目的镜头,特意减小了画幅,做成了类似“家庭影像”的感觉。这种方式同样很有趣。这几个镜头真的分不清是资料画面,还是摄制组组织拍摄的。不过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传达给观众的信息。这里传达给观众的就是:这是日常的家庭影像记录。
这里给我的启示:即使是组织拍摄的画面,也可以用小光圈的深景深模拟手机或家庭DV的效果,后期降低画质,模仿“家庭影像”。这种影像,比那种高清的、浅景深的、很有质感的影像,要显得更真实。《第九区》那种模拟新闻的拍摄手法和调色,也可以借鉴学习,在合适的地方形成“真实”的表达。
不过话说回来,《72岁的一个晚上》这个地方的一组蒙太奇,只有几个同一个地方不同水上项目的剪辑,看着给人感觉就是到一个游乐场摆拍且是赶着拍摄的,如果多换几组镜头,山里、海里,滑雪、跳伞、穿越等等都安排上,就更好了。如果真的有不同时期的镜头会更好。邱必昌在前面说的是“从小就皮”,给观众的期待是,想要看到他小时候“调皮”的镜头,但是后面给出的镜头是老年的邱必昌,而且看发型以及头发花白程度,根本就是近期的镜头,所有又增加了排演摆拍的嫌疑。所有我觉得这几个镜头,干脆不加,还要更舒服。
我在看这几个镜头,就直接出戏了,可能普通观众可能不会这么苛刻吧。但是我始终坚信一点:别把观众当傻子,别试图糊弄观众。制作者的诚意,一定是可以被看到的。
另外,作为剪辑师,我在剪辑的时候,通常会非常审慎地给观众期待,因为一旦给出期待,就一定要回应,不然就会转化为失望。失望是比平淡更负面的情绪。当然,绝不能不给观众期待,不然观众不会有继续往下看的动力,关键的是,要在后面合适的时间,满足观众的期待,不能太早也不能拖太久,要恰到好处地撩到观众的痒处。
上一个镜头里,也就是第一个镜头,叙事效率其实挺高的。一个能和年轻人一起玩,爱泡吧,爱爵士乐,爱喝红酒的油腻老年人形象已经塑造起来了。第二个镜头(把插入性的蒙太奇也算在内),强化了这个人爱玩的标签。
接着的镜头,朋友指着镜头,同样是打破第四面墙,向观众介绍邱必昌:你只要让他能够想得到的,你只要让他能够听到的,他觉得好玩,他马上就去做。接着就是一组打手鼓的镜头。
视频用“人物口述+佐证画面”的形式,就是说一句,然后立刻用相关镜头证明一下。这种塑造人物的方式,效率是很高的。
夜店(心态年轻)+爵士乐、红酒(有格调)+口述爱玩和水上摩托(爱玩、年轻)+朋友口述爱玩和手鼓(爱玩、随性)。
可以看到,人物的形象是一层层不断深入、不断强化的。
短片塑造人物,需要很高的叙事效率,先不要想着把人物塑造的多么立体多么丰富,首要的是足够“鲜明”,要给人物一个标签,然后不断强化。因为观众在短片的篇幅限制下,不可能去“凝视每个个体的深渊”,而是走马观花,看过能留下印象就算创作者的胜利了。
手鼓的镜头之后,回到邱必昌的访谈镜头。这里的台词,传达出的是:不攀比,有酒今朝醉的及时享乐主义。
然后是另一个朋友说邱必昌不在这里(玩手鼓的地方),就在酒吧带着姑娘玩,夜生活比他(一个年轻人)还丰富。然后就是邱必昌夜场蹦迪的镜头。然后回到执之前朋友的介绍:每到周五逛啤酒吧。再接着回到手鼓教室朋友介绍:不在这里,也不在酒吧,就在国外。
接着,回到邱必昌访谈镜头:依然是及时行乐的思想。中间穿插游玩路上的镜头。
然后介绍近五年迷上了潜水,吹嘘自己潜了600多瓶(氧气罐),接一个潜水的镜头,接朋友介绍和邱必昌一起潜水的经历,接潜水镜头。
然后回到酒吧那个一开始出场朋友介绍:人的生命力怎么可以那么旺盛?
岔开一笔,我个人不喜欢这个人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泡吧,夜生活,潜水……爱玩,哪怕是人老了还爱玩,都不算什么生命力旺盛吧,因为做的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
然后回到邱必昌的镜头,一边摘菜一边介绍自己不规律的生活作息:晚睡晚起,下午三点第一顿早饭,七八点第二顿,半夜第三顿,喝酒到三四点。
然后回到朋友介绍:之所以邱必昌活成这样,是因为他是邱岳峰的儿子。
朋友接着的一通介绍就不详细记录了,大概就是:那个贫乏的年代,家里养了很多观赏植物,火炉子上煮着咖啡。
所以,有个厉害的父亲,从小过着小资的富二代生活。
回到邱必昌的访谈,他说:父亲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辈子,很快一晃就过去,所以一定要做两件事情,一要为社会做点儿什么留下点什么,二要尽可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好一点。
这个片子不长,13分钟。虽然是刻意想要拉片,思考一下人物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不过看到这里我已经看不下去了。
后面就是邱必昌自述、朋友介绍、邱必昌和朋友在酒吧喝酒聊天。不耐烦看,快进了一下,后面尽是老了还爱玩之类的BBB。
然后女儿来接邱必昌回家,朋友把他送上车,转身对着镜头说:他是给生命找着了一个理由,所以,他知道怎么活,哈哈,那么我们接着喝。
黑场,全片结束。
3、小结
也许是拍摄条件受限,这部片子没有几个场景,酒吧、疑似邱必昌家里、玩手鼓的地方,基本就没有了。以访谈的形式建构,不同于其他片子的是打破了第四面墙。本来想认真拉下片,因为第一个镜头设计的很高效,结果后面谈话内容太无聊了,整片我是没耐心看完的,很失望。但是一些思考,一些镜头和表达方式,都是可以借鉴的。
纯粹以谈话的形式来构建一部片子,像《这个男人来自地球》那样,很难。纪录片以谈话来架构,也很考验剪辑师,《72岁的一个晚上》后面的谈话就剪辑的很无聊,看不下去。
当然,价值观的不认同,可能才是我看不完这部片子的原因。胡适说孔子最伟大的精神有两点,一点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点就是“不知老之将至”。不服老,不向生命妥协,是最宝贵的精神,但是老了吃喝玩乐多数时候是“老不正经”。我认识的前辈们,不向岁月妥协,为时代留影像,为科学做贡献,像邱必昌父亲邱岳峰说的那两点的第一点: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这样的人,值得尊敬。
把人生的侧重点放在邱岳峰所说的第二点上:尽可能把自己生活安排好一点。那是他人的生活方式,不值得指责,但也不值得尊敬。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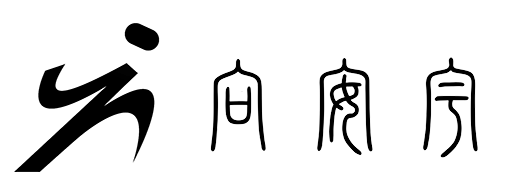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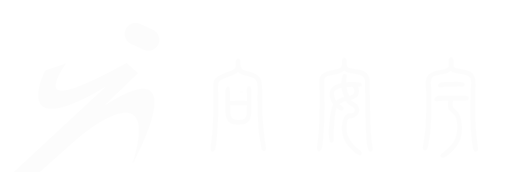
请登录以参与评论
现在登录